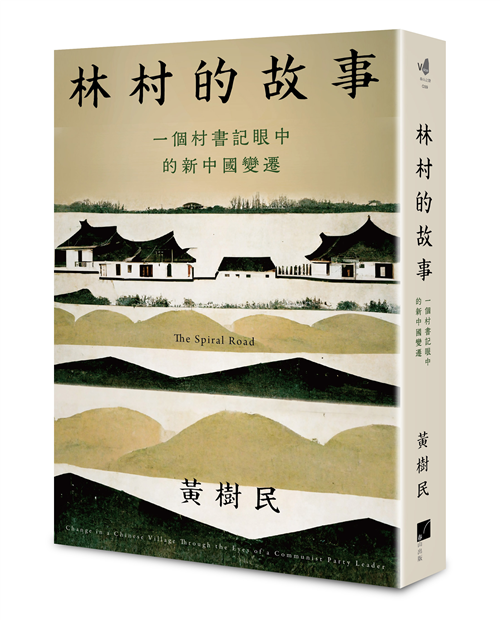
一版序
二版序
三版序
誌謝
本書主要人物介紹
前言
第一章林村印象
第二章家族歷史
第三章解放
第四章饑餓歲月
第五章參加政治運動
第六章返鄉
第七章治保主任
第八章欣欣向榮
第九章解體
第十章農村幹部
第十一章一九九○年代的變化
第十二章林村何去何從?
第十三章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林村
參考書目
附錄
彩頁說明:二○一五年的林村
第五章 參加政治運動
【政治運動】
第二天早上我吃了早飯就到葉書記家去,我實在迫不及待想繼續談他參加政治運動的事。
葉書記正在廚房幫他太太寶珠準備豬食,把番薯葉切片和番薯簽同煮。寶珠一如往常地向我打個招呼,之後便不發一語。村中婦女的不成文規定,是要順從丈夫,至少在公共場合要做到這一點,對此寶珠可說是恰如其分。在我住在林村的這段時間,她一直是不置可否,除非我直接問她問題,否則不會開口。但是這一天,我很高興寶珠也在場,因為我也想問清楚她在四清時的經歷。
我向他們兩人問道:「在四清的時候,你們有沒有見面?」寶珠假裝沒有聽到,繼續攪著豬食。回答的是葉書記。
「在四清的頭一年,我很少看到寶珠。我們雖被派到同一縣,但是所在的公社不同。她被派到灌口鎮的第三公社,兩地的交通不方便,而且我們也因政治任務在身,無暇分神。但是到了放假,她回泥窟村,我要回林村的時候,我們會找機會見見面。我一得空就回村裡,把攢下來的薪水交給父母貼補家用。我告訴過你在工作隊的時候,我一個月可以得到二十七元人民幣。我要交給房東九元,別的零星花費,像肥皂、香菸,喔!對了,糖等等,大概要二到三元,所以大概可以存個一半交給父親。那時我家的人口變多了,我最小的弟弟在一九六三年出生,所以我一共有六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父親要賺足工作點數餵飽全家人實在不容易,所以我弟弟大多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而必須盡早開始工作補貼家用。」
「你多久回林村一次?」我問。
「大概一個月一次。」葉書記答道:「因為四清的時候我常常回來,所以比較清楚這個運動對本村的影響。派到本村來的工作隊,一下子就把大隊黨支部書記鴉片洪和大隊長雷公林搞下來。工作隊到達之前,雷公林還開了個玩笑,說工作隊既然要三同,要和農民併肩工作,那我們得先做些特大號的馬桶讓他們用扁擔挑才行。這其實是在嘲笑這些『城市孩子』吃不得苦,沒辦法和我們下田做一樣的工作。但是工作隊在調查大隊幹部疏失的時候,農民把這句玩笑話也報告上去。結果工作隊特別針對雷公林開了個鬥爭大會,雷公林被打得死去活來還革了職。」
「在這次的政治運動裡,有沒有其他人被攻擊?」我問道。
「幾乎每個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受到波及。」葉書記一邊回答,一邊將煮熱的豬食舀入提桶之中:「但是林村的人受影響最深的,恐怕要算是吳家兄弟。運動剛開始時,田雞吳和他哥哥吳明都在江頭公社做事,但是上級命令他們回林村,他倆一回來就受到村民嚴厲的偵訊。因為田雞吳在解放前經常變節,又與各方關係良好,所以連一點還嘴的餘地都沒有,就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他還有一頁不大光榮的歷史,就是他在加入解放軍之前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兵。他為什麼要叛離國民黨,加入解放軍?是不是要做國民黨的間諜?這類的問題一經提出,田雞吳毫無招架之力,所以就成了個政治案件。」
寶珠靜靜地用扁擔挑起兩擔豬食出去了,廚房裡只剩下葉書記和我兩個人繼續講話。
「田雞吳的命運至此起了大轉變,」葉書記的話中有一絲復仇的快感:「工作隊要他寫自白書,所以把他單獨關了好幾個月。但是他是個文盲,根本寫不出來。工作隊對他的口供不滿意,所以常常毒打他。工作隊希望這個案子有個重大突破:讓田雞吳招認他是國民黨派來,潛伏於此地的間諜。田雞吳大概從來沒有想到,解放了以後他還要吃這種苦頭。他走投無路,想用皮帶上吊自殺,了結自己。但是被看守的人發現,把他救活了。但是說也奇怪,田雞吳這條命撿回來之後,人變了很多。雖然今天你看他這個人還是講話帶刺,態度傲慢,但是比起他被監禁之前,可是大大不同了。他這一生,起伏實在很大。
「在四清的時候,村裡還有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一直到近幾年才解決。這件事和林家的長房林大有關係。林大家裡原有不少田產。在抗日戰爭之後,林大的父親決定分家,四個兒子都一樣,每人分到大概二十畝田(約一.三公頃),林大這個人,做事勤快,用錢也很謹慎。」
葉書記在大灶裡添了些柴枝,從水缸裡舀了些水到鍋中,放些番薯葉進去,準備再煮一鍋豬食。他邊做邊說:「但是他的三弟─林山,從年輕時就游手好閒,大家都知道。林大結婚後,林山也娶了老婆,生了兩個孩子,坐吃他父親分給他的二十畝田過日子。他僱了他老婆最小的弟弟來做田裡的活兒,但卻跟這位小舅子的老婆發生關係,兩人私奔到廈門去。到了廈門,他又拋棄這個女人,整天吃喝嫖賭,無所不來。到了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他的田產也花光了,於是淪落到在廈門街上流浪乞討生活的地步。」
「那他的老婆孩子怎麼辦?」這三人的生活,恐怕才真正成了問題。
「林山的妻兒?」葉書記一邊攪著豬食,一邊回答我的問題:「眼見賴以維生的田地被一一變賣,自己實在不知如何度日,林山的老婆是娘家嫁出來的女兒,不能回娘家求援,她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殺。幸而她的兒子,發現她舉止異常,通知她那一代輩分最高的長兄林大,把她救活了。後來林大就把弟媳婦一家接來和家人同住,一起在林大的田裡工作,說起來林山的兩個兒子都是林大養大的。
「解放之後,林山回到村裡來,他被劃在貧農階級裡。他和政治權力沾不上邊,因為村裡的政治全為吳家兄弟所把持。後來實行土地改革的時候,並沒有人找林大的麻煩,因為林大的田地雖然有二十畝之多,但是家裡吃飯的人也多:除了林大夫妻倆,還有林山的妻子,林大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再加上林山的兩個兒子,一家十口人,地有二十畝,算來仍算中等,所以被劃為中農。」
「你剛才不是說,這家發生了什麼不公平的事嗎?」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葉書記要把林家的人口和田產交代得這樣清楚。「在一九七八年前,階級劃分是非常要緊的事。」他憤憤不平地說:「林大這條命,幾乎斷送在他弟弟林山手上的。林山趁著四清時加入了貧農協會,開始奪權,並且把矛頭指向他看不順眼的人。審判田雞吳的時候,他出了不少主意。之後,他又要求重新審查他親哥哥的階級地位。林山堅稱林大不應劃為中農,而應該是富農。他辯稱林大家有二十畝田,但是只有七口人,林大夫妻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另外那三個人,也就是林山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其實是林大僱用的長工。加上這三個雇工之後,林大的剝削程度便超過二十五%,所以應該歸為富農階級。」
「但是這樣講不對呀!」我不禁說道。
「當然不對,」葉書記諷剌地說:「林山這些話一說出口,全村同感震驚。要不是林大,林山的妻兒哪有今天?怎麼會有人這樣子恩將仇報,不仁不義?這個人做出來的行徑正好和全村的人心裡想的相反。連丟掉差事的前大隊黨支部書記鴉片洪,都難以置信地評道:『林大救了弟媳婦,又把她和姪兒接來同住,這種善事要是算作是剝削他們,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天理?』村內的公論都倒向林大這一邊,但是林山有工作隊做靠山。林山現在是個積極分子,在工作隊的支持之下,他終於如願把他哥哥劃成富農階級,村裡多了一個階級敵人。」
「林山當權多久?」我問道:「四清一共持續幾年?」
「大概兩年左右,後來爆發文化大革命,取代了四清。」葉書記答道:「那時候林山也對他堂弟林柏亭落井下石。林柏亭就是胖林,他在土地改革的時候已經被劃作富農,一有政治運動,他就吃不少苦頭,他無可奈何,只能盡量順從忍受。胖林有幾個住在南洋的表親,不時寄錢或是食物、用品給他。胖林大概是一方面想改善和幹部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想證明這些包裹裡沒有其他的東西,所以會送一些給大隊的幹部。早先是送給吳氏兄弟,後來送給鴉片洪和雷公林。到了四清的時候,林山說這是胖林想博得幹部個人的好感,根本就是在賄賂,所以,黨都變成了封建地主的工具了。因此在接連幾次的鬥爭大會中,胖林都受到審判,被罰做全村最吃重、最骯髒的工作,像是疏通水溝或是清理公共廁所。」
這時候,寶珠挑著兩個空桶子進來,我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問他們兩個:「四清的時候,你們在龍海待了多久?你們在那裡做什麼事?」
寶珠仍然不發一語,好像沒聽見我的話一樣,葉書記大概是以為我在跟他說話,所以由他來回答:「我在龍海縣鄉下的工作隊待了一年。在一九六五年末,被調到海倉縣,在穀物儲存機構中推動社會主義運動。接了新工作之後,生活條件改善很多,至少每餐都有粥可吃。另有一個姓黃的人和我一起到任。這個姓黃的人很胖,原來是人民解放軍的政委。軍隊中的政委地位很高,特權也多。他大概從沒想到他竟會有今天,落到這種地方來生活。他每頓飯要吃八到九碗粥;你知道,如果食物不含油脂的話,人的食量就會變大。吃飯的時候,我和他同桌吃飯,不和農民一起。我的胃沒有姓黃的那麼大,所以吃的也沒他那麼多。有的時候,我明明已經飽了,還得裝著在吃飯的樣子。要是我把碗筷放下來,他馬上就不吃了。沒有人要他這樣,但是這個運動的目的,既然是糾正幹部的不當疏失,每個人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本身突出的行為。」
「你在海倉鎮待了多久?」我問。
「大概只有兩個月。」葉書記答道:「一九六六年一月,我被派到集美鎮,這個地方在大陸上,面對著廈門島。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鎮上的國營工廠推廣社會主義教育。在國營廠工作的年輕工人大多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沒受過多少社會主義教育,所以我們就要啟發他們的社會主義意識,將他們組織起來,加入政治系統之中。這些組織裡,最有效的當數共青團。我們會舉辦活動吸引年輕人,並導正他們生活的軌道。
「白天的時候,我都在國營工廠上班,例如說到百貨部去賣東西,或去食堂的廚房煮飯。我和工人們一同工作、吃飯和休息。由於堅持三同,我很快便贏得了工人們的信任。到了晚上,我便帶領這些年輕人學習,學習念書寫字,或是學習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或是學習政令宣導。有時,我會帶他們做些娛樂活動,像是打場球,或是唱唱革命歌曲之類的。一旦成功地在廠內成立一支共青團的支部,我就動身到另一個國營廠去。」
「你是因為這段經歷,才和許多地方幹部結為知交嗎?」我開始有點瞭解葉書記的觸角為什麼會伸得那麼廣了。
「是啊!那真是我生命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他的眼神既驕傲又滿足:「我對工作完全投入,所以在一兩個月內就會看到自己的成果。在不同的國營廠工作,也使我對各行各業更加瞭解。和年輕人工作,真是太有趣了。
「我還記得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件令人好笑的事,我們的運動手冊上面要求我們舉辦『憶苦思甜』大會,以便加強年輕人的『社會主義意識』。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讓年輕人熟悉解放之前群眾生活之苦,並且拿來和共產黨帶給他們的甜美、富足的生活做一比較。一般而言,我們會尋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生活貧苦的人。如果這個人的生活在解放之後大有改進的話,我們就會邀請他來和年輕人講講話,談談以前的『苦』和今日的『甜』。
「在集美鎮上有個退伍軍人。我們聽說他出身於北方的貧窮人家,家裡窮得把他賣給有錢人做童僕。他每天從早忙到晚,吃不飽、穿不暖,要是做家事犯了什麼錯誤,還會被重打一頓。最後他終於受不了,逃走去參加人民解放軍。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已經退休,每月照領國家退休金,日子過得很悠閒。我想,讓年輕人聽他的經歷,是再適合也不過了。所以我就辦了個『憶苦思甜會』,請他來做演講。他很生動地描述解放之前生活的種種困難。他小的時候沒吃的、沒喝的,連遮風避雨的地方都沒有。他是賣身來做童僕的,主人、太太、小主人,連較為年長的僕人都常常對他拳打腳踢,這般這般,一直說下去。然後他開始講解放以後過的好日子,一一指出一九五○年代初期生活上的改善。我心裡想著,這個會開得真是順利,年輕人一聽就知道他話裡的意思。我心裡得意起來,覺得又完成了一項任務。
「但是接下來,糟了!這個老傢伙該停不停,一直講下去!他開始講在大躍進之後日子有多苦:他餓得有多厲害,看到多少人死亡。我想阻止他,但他是以貴賓身分受邀來此演講,而且他又是個榮譽退伍的軍人,我實在不敢冒犯。我看看觀眾,他們早聽出演講者話裡的毛病,正津津有味地聽著。我看到有幾個年輕人竭力忍住以免笑出聲來,我自己也開始覺得好笑。會議開完以後,我跟上級報告這件事,他也大笑不已。」
「那段期間你做了多少件工作?」我問道。
葉書記扳著指頭算著,回答說:「在一九六五年後半年和一九六六年的前幾個月這段時間,我在六、七個國營廠待過。我藉著這個機會認識了許多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低層的幹部。這些人現在都做到了機關首長。我和他們深厚的交情,成為我自己重要的政治資本。還有,因為我努力推展社會主義運動,成效卓著,一九六六年三月,我獲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真的很感謝黨的提拔培養,讓我得到這份殊榮。我父親是個低下的窮種田人,到我這一代,竟然能成為共產黨黨員!你想想看,我竟能和極少數通過考驗的人平起平坐,而且被認為是黨內下一代的中堅!我雖然不見得能全然認同這個政治運動中的濫權和恐怖的治術,但是毛主席和黨的指示是正確的,我應該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對。這些濫權和恐怖政治可能是別的原因造成的,只是我還不瞭解罷了。」
「寶珠是在那時候獲准入黨的嗎?」我問。
「是的。」葉書記答道:「在四清的時候,有一百二十名左右的積極分子獲准入黨,包括寶珠在內。我們這一百二十名新黨員都先在地區總部所在地的集美鎮集結,等待上級發派下一個工作。四清運動已圓滿落幕了,可以預見我們這些少數的優秀分子必定步步高升,前途未可限量。不用說,當時沒有人覺察到地平線的彼端醞釀著風暴,即將完全扭轉我們的命運。等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一切都改觀了。」
語末,葉書記的聲調愈來愈低,彷彿因為久談而疲倦,或者他想避開不談那些從不給外人知道的事。我看不出他臉上有任何表情,因為在廚房的這一角沒有窗戶,光線暗淡。我想,今天就談到這裡吧。
▌一道當代中國的縮影,一本小說般的民族誌。▌
●當代中國研究的民族誌經典●
***
【自從出了這件悲慘的事情,我開始問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像侯桐這樣年輕、善良、健康、精力充沛、受歡迎的人,都這麼不走運,那麼,難道我就比他強、就配有好命嗎?如果到頭來不過是生病受罪、一命嗚呼,我為什麼還要玩命工作?有兩個月的時間,我盡量不待在林村。一在村裡,我就想起侯桐去世前的幾個月受的那份罪。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廈門市的卡拉OK飯店能讓人舒坦一下。你可以長時間待在這裡吃飯,還有高級音響,可以找到年輕時唱的革命老歌。唱這些革命歌曲,我的生活就有目標,就有希望。我現在是一個好歌手,你信不信?】
***
一九八四年,原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系任教的黃樹民,來到廈門市郊的林村,準備展開田野調查,希望以該村為範例,具體而微地呈現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由上而下頻繁颳起的政治運動旋風和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平凡微末如林村的農村社會,如何度過並適應各種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個溼熱的十一月天,作者與該村的黨支部書記,亦即村中的統治者葉文德初次見面,為了討論房租(但葉並不是房東),結果可說不歡而散:「一百塊美金!我真是氣極了,他竟然開出這種不合行情的價錢。我突然有股衝動想把桌上那盤蜜餞砸到他臉上。」哪知峰迴路轉,葉文德因父親墳墓被毀向作者訴苦,開啟兩人深談契機,最後作者更決定以這位村書記的個人生命史為主線,織連《林村的故事》。
上述過程生動地描摹在本書開篇,使我們立刻意識到,這是一本不尋常的民族誌──作者將不會隱身在故事背後,僅以旁白式的畫外音,進行分析解釋;反之,作者讓自己也成為故事中的要角。
《林村的故事》以作者和葉文德一問一答的對話形式推展,徐徐揭示林村自一九四九年後所受的衝擊與回應;由於筆調流暢,情節曲折,令人似在讀小說,常被譽為不只是扎實的學術研究,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甫出版就成為經典。
第二版增補了作者於一九九六年回訪時的觀察。此時葉書記五十開外,村子在其領導下欣欣向榮,他本人事業也很成功,但心中茫然卻日益增多,開始流連在村外的卡拉OK飯店,唱舊時革命歌曲尋求安慰。
本書為最新的第三版,作者將二○一五年重訪林村的感想補寫一章,以期讀者體會當前中國改變的速度和趨勢。已富裕到全村四百多戶至少有十戶財產超過人民幣一億的林村,其未來有無隱憂?卸下了書記職務的葉文德,現況又如何?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林村,仍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當代中國縮影。
黃樹民
長期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現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二O一O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二O一五年獲中華民國總統科學獎。著作有《借土養命:從雲南到金三角,從毒品到永續農業,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族誌》(春山,2021),譯作有《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春山,2020)。
第三版序
黃樹民(序於二○二二年七月)
二○一五年,我卸下學術行政工作,並準備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退休時,便開始期待閒雲野鶴般的自在生活。在規劃盤算之際,突然想到,何不利用時間抽空到林村待上一段時間。除了拜訪往年舊友之外,還可以將我以前在林村拍攝的幻燈片,放映給他們看,一起共同回憶往事。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我在林村住了七個月,那時,中國才改革開放未久,我仍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任教,是第一批中國允許進入農村進行深入田野調查的少數外來研究者;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我再度回到林村住上五個星期,在此之前,我每次的回訪都很短。在這兩段較為長期的田野調查中,我一共拍攝了五百多張的幻燈片,記錄當時的生活面貌,如今回看,可說是為村子留下一些稀有的歷史影像。尤其,當年貧困的林村並沒有照相館,連一臺相機都沒有。
這個念頭一生出來,我就開始整理擱置在檔案櫃中許久的幻燈片。只是,要放映這些幻燈片時,才發現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我當初去田野時所使用的一些影音設備,大多已被淘汰。不但拍攝幻燈片的照相機已鮮少人用,放映幻燈片的放映機更是宛如絕版,難以取得。經多方探詢,終於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博物館找到一臺還能使用的投影機,商借出來使用。博物館管理員知道我要帶著這臺古舊且沉重的放映機到中國放映幻燈片時,還特地幫我準備一個二百二十伏特的電壓轉換器和多個備用的幻燈機燈泡,以防兩地電壓不同對放映機或燈泡造成傷害。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我抵達林村,準備住上三個星期。書中的書記主角葉文德先生請現任的村委書記林阿里先生安排我住在村內的大飯店,這是村裡合資新建的二十七層樓大飯店。飯店位於全村的中心點,很方便我提著幻燈機和幻燈片,走訪村民的家。入住旅館之後,我就開始聯繫一些老友,準備登門拜訪,並安排放映幻燈片給他們看。
說來好笑,正如民族所博物館那位管理員的預測,這臺老舊幻燈片放映機頻頻出現問題。有時是放映機或變壓器過熱,冒出煙來,只能趕快關機,免得機器損壞。有時是燈泡燒掉,只能換上新燈泡。常常是才放映幾分鐘,就得停下來,不是得讓機器冷卻,就是更換新燈泡。但即便困難重重,村民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尤其年輕一代更是興奮。當他們看到上一代父執輩衣著簡陋,冬天打著光腳在田裡工作,或是在簡陋的工廠裡從事粗活、操作工具時,都發出驚嘆之聲。甚至,村子內外普通的田園景像,像是村邊菜園和遠處背景的山丘,都令他們驚異。滄海桑田,當前的林村不但本身高樓大廈林立,也被附近的外村高樓包圍,放眼望去,根本見不到農耕田地和幾公里外的山丘。對村內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一代來說,農地和山丘早已不是他們生活圖像中的浮光片影。
從一九八四年起,到後來陸續的追蹤訪談,我在林村的田野調查紀錄,可說是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驚人變化。在物質生活上,一九八四年的林村還是個遠離廈門市區十公里外的簡陋農村。那時,農民赤足下田,住在簡陋的磚木平房裡。三、四位頭腦靈光的村民把握機會,搭上改革開放的便車,籌集資本購買一臺二手的解放牌卡車或農用拖拉機,就開始幫人運送物質,賺取勞務工資,開始發跡致富,成為「萬元戶」。有了點錢後,他們又籌劃蓋建傳統閩南式的兩層樓石板屋,開啟第一波的建築熱。當時,能通行大貨車和大客運的柏油路還未接到林村,從市區搭乘廈門市郊公車到一公里外的洪山柄就得下車,然後走完這段泥土路,才會進村。那個年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兩條腿外,就是自行車和三、四輛的摩托車。
一九八○年代,整個林村只有村辦公室有一臺手搖的有線電話機,而且經常不通。電風扇、電視機或電冰箱等家電,都是村民們嚮往而不可得的奢侈品,除了需要付出巨額的現金外,還得搭配政府配給的工業券才可能買得到。當時中國的境外人士很稀少,而我又有臺灣與美國的背景,成為村民好奇與關注的目標。在與村民閒聊時,他們最常問我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在美國大學教書,一個月的工資是多少?」我的回答必定引起他們一陣驚呼,直說比中國大學教授的工資高出百倍。第二個常有的問題則是,「在美國,一對夫妻可以生幾個小孩?」當我回答美國並無具體的生育政策、也不限制可以生育多少子女時,又會引起另一陣驚呼。對這些剛從嚴密控制的集體公社制中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而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似乎還在他們想像之外,也還未構成他們認定的基本公民生存權的一部分。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民,才剛掙脫極權政府的專斷控制,要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還有待時間的蘊育和持續的爭取。
中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大力推動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漸除卻了銬在全國人民頸上的枷鎖,給予他們一點基本的人性尊嚴和生存的驅動力。其具體的成就,即如林村三十多年的改變所彰顯的,是不斷改善的生活條件、強大的生產力、寬鬆和諧的人際關係,以及較為理性的社會治理。在這樣的變遷下,林村與外界的重大差距,已逐漸消失,生活水平甚至超越中國的主流社會。
二○一五年,我在一場林村的宴席中,半開玩笑地請問在座的村民,全村四百多戶中,有多少戶的家庭資產超過人民幣一億元?他們仔細討論後,告訴我至少有十戶之多。同時他們也指出,村政府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提供給少數幾戶的貧病村民每月至少人民幣五千元的生活費。所以,村內不存在真正衣食無著的貧困戶。
以林村的歷史來看,這一代的中國青少年,無疑是幸福的一代。他們不像父祖輩般經歷過國共內戰的血腥、土改的暴力、大躍進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鬥爭。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他們看到的是平淡但衣食無缺的生活,低調但卻逐步寬鬆的言論控制,專權卻開始注重民意的共產黨,和一個似能保證不斷改善的未來。「社會主義的優異性」,似乎在中國大陸得到證實,也被這一代許多青少年接受、擁抱。
換言之,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們似乎看到在中國大陸一個運作合理的公民社會萌芽,似能將帝制中國遺留下來的專斷、殘暴、不公平、非理性,逐漸削減、排除,甚至透過市場化的社會主義治理,走向馬克思夢想的烏托邦。
不幸的是,中國大陸這個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夢,現在似乎已夭折,甚至早已胎死腹中。近年來,中共官方對一般民眾的言論、思想、行動控制,逐漸收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鋪天蓋地而來的領袖崇拜、政治學習、社會動員、檢舉上報、輿論控制等,又逐漸成為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新常態。那些中國社會中的有為菁英,才勉強掙脫出紅衛兵瘋狂暴力的陰影未久,如今再度被噤聲。初嘗基本公民權的平民百姓,在面臨無軌跡可循的黨政暴力衝擊時,基於人身安全的恐懼,只能選擇放棄或逃避,而非據理力爭。最近中國的「潤學」當紅,移民海外成為民眾心願。
在林村,最近幾次中國政府推動打房政策,房地產較多的村民選擇躲避到香港、澳門或海外渡過難關,亦可見一斑。有的村民選擇消費型的自我麻醉,包括酗酒、吸毒、睹博等。當然,仍有一些村民堅持舊有信念,繼續從事公益服務和社區改善的工作。
林村是近百萬中國農村中的一個經典縮影。我有幸在林村的轉型過程中,目睹並記錄下來它所經歷的波瀾起伏和日常剪影,留下一點歷史回憶。作為凸顯中國發展的時間與空間縮影,林村的經驗對我們有兩個啟示。在時間上,林村可說是改革開放的快速版,告訴我們理性適當的公共政策和措施,如何可以加速社會發展,造福群眾。從空間上來說,林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濱海條件,搭上改革開放的大浪潮,順勢取得令人讚嘆的經濟成果。
不過,林村過去四十年來得以成功的時空際遇,現在卻面臨新興的未知數和政經挑戰。這個我曾有幸參與記錄村民生活與夢想的村子,如今已大樓林立,但仍保有村落型態的人際網絡與無形界線。未來能否繼續順利轉型,克服變幻莫測的政治力量,我衷心祝福並拭目以待。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出版社: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9-14
ISBN:9786269612963
定價:500元 特價:79折 39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