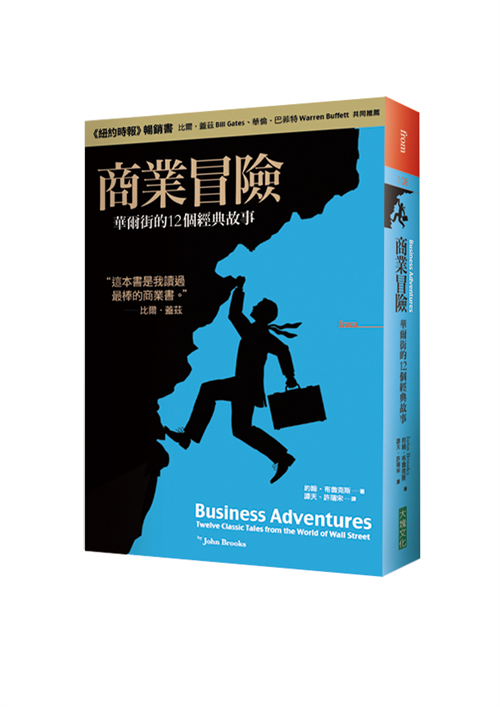
第1章 股市的波動 一九六二年的小崩盤
第2章 愛德索的命運 一個值得警惕的產品故事
第3章 聯邦所得稅 它的歷史與特性
第4章 合理的時間 德州海灣硫磺公司的內部人
第5章 全錄,全錄,全錄,全錄
第6章 讓客戶圓滿 一位總統之死
第7章 企業裡的哲學家 奇異的溝通問題
第8章 美股最後一次大囤積 一家叫做「小豬商店」的公司
第9章 華府高官的第二人生 商人大衛‧李蓮道
第10章 股東會季節 年會與企業權力
第11章 免責咬一口 一個人、他的知識與他的工作
第12章 英鎊捍衛戰 銀行家、英鎊與美元
第5章 全錄,全錄,全錄,全錄
當世上第一部油印機(mimeograph machine)──第一部實用於辦公用途的機械式文件複寫機──於一八八七年問世時,推出這種機器的迪克公司(A. B. Dick Company)並沒有在美國引爆一場熱潮。事實上正好相反,在芝加哥創辦這家公司的迪克先生,碰上一個難以克服的行銷問題。原本經營伐木的迪克,由於每天用手抄寫報價、寫得厭煩透頂,本想自行發明一部油印機,最後他從油印機發明人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手中取得製造權,開始生產油印機。他的孫子小馬修斯‧迪克(C. Matthews Dick, Jr.)說,當時「大家不想為辦公室文件複製許多拷貝。」迪克公司現在生產各式各樣辦公室影印與複印機,還包括滾筒油印機。目前在公司擔任副總的小馬修斯‧迪克說:「最先使用這項東西的,大體上是教會、學校與童子軍這類非商業組織。想招徠公司與專業人士,祖父與他的同事必須費盡周章。當年辦公室運作型態早有定規,要人用機器複製文件,是一種打破這種定規、讓人遲疑的新觀念。畢竟,在一八八七年,打字機上市不過剛滿十年,使用並不普遍,複寫紙的使用情況也一樣。一位商人或律師若需要拷貝五份文件,他會找書記用手抄寫。許多人會問祖父:『為什麼我要做一大堆拷貝,堆得到處都是?這麼做只會把辦公室搞得凌亂不堪,只會惹來一些偷窺,還浪費了好些紙張。』」
在另一個層面上,老迪克還面對了一個或許與名聲有關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文件圖表的拷貝,一直給人一種大致不佳的印象。英文裡當作名詞與動詞使用的「拷貝」(copy)這個單字,有許多負面意涵。《牛津英語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明白指出,在過去幾百年間,「拷貝」這個單字帶有一種欺騙的氛圍。事實上,從十六世紀末直到二十世紀初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拷貝」與「偽造」(counterfeit)幾乎是同義詞。﹝古早以前,「拷貝」做名詞使用時,原本有一種「充分」(plenty)或「富足」(abundance)的正面意義,到了十七世紀中葉,這類用法已經逐漸式微,只有形容詞形式的「copious」(豐富、大量的),仍有這類正面意義。﹞
十七世紀法國箴言作家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於一六六五年在他的《箴言集》(Maxims)中寫道:「只有能將劣質原始文件的缺陷展現的拷貝,才是好拷貝。」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藝評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也曾在一八五七年斬釘截鐵地說:「永遠都別買複製畫。」而且根據他這項警告,不買複製品不是因為這麼做等同欺騙,而是會自貶身價。再者,書面文件的拷貝也往往啟人疑慮。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一六九○年寫道:「一項文件紀錄經過公證的拷貝,儘管可以視為有效證物,拷貝的拷貝卻永遠無法充分佐證……不能作為呈堂證供。」大約在同時間,印刷業崛起導致「foul copy」一詞的出現,意思是「充滿訂正修改的草稿」。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還流行一句話,說一個人或一件物,是他人或他物的「pale copy」,也就是「劣質拷貝」。
工業化造成大量複印需求
不斷工業化造成的實際需求,無疑是這類態度在二十世紀出現逆轉的主因。無論怎麼說,辦公室文件的複製需求,開始非常迅速地成長。(或許,似乎讓人感到矛盾的是,這項成長與電話的崛起同時出現,但也許這種現象並不矛盾。一切證據顯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論使用什麼溝通工具,都不會僅僅因為已經完成溝通目的而打住,它總是會讓人覺得更需要溝通。)一八九○年以後,打字機與複寫紙開始普及,滾筒油印也在一九○○年過後不久,成為辦公室的標準作業程序。迪克公司在一九○三年理直氣壯地表示:「沒有愛迪生油印機(Edison Mimeograph)的辦公室,不是設備齊全的辦公室。」美國的辦公室在這一年已經擁有約十五萬台油印機;這個數量到一九一○年可能突破二十萬,到一九四○年高達近五十萬。
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膠印機(offset printing press)問世,由於複製的產品比滾筒油印機精美得多,遂成功取代了油印機,成為大多數大型辦公室的標準裝備。不過,就像油印機一樣,膠印機在展開複製工作以前,也必須先製作一張特定主版頁(master page),而主版頁的製作不僅成本較高、也比較費時。也因此,唯有在需要製作相當數量拷貝的情況下,使用膠印機才合算。套用辦公室裝備術語而言,膠印機與油印機是「複寫機」(duplicator)而不是「複印機」(copier),而所謂「複寫」與「複印」之間的界線,一般以十到二十份拷貝之間作為區分。有效又省錢的複印機,花了極長一段時間才姍姍來遲。無須製作主版頁的各式影印裝備,在一九一○年左右開始問世,其中最有名的是佛特斯泰(Photostat)影印機,直到今天情況仍然如此。不過,由於成本高昂、製作速度緩慢,而且操作不易,它們的用途大體上局限於建築、工程構圖與法律文件的複製。直到一九五○年過後,拷貝一封商業書信或一頁打字稿的唯一實用機器,仍然是一台滾筒上裝了複寫紙的打字機。
一九五○年代是辦公室機械化複印作業的草創期間。在短短一段時間,市面上突然出現一堆各式各樣、能夠複製大多數辦公室文件的裝置。這些裝置不需要使用主版頁,而且每製作一份拷貝頂多只需要一分鐘,成本也只有幾分美元。這些裝置運用的技術各不相同,比方說,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生產的熱感複印機(Thermo-Fax),於一九五○年問世,使用熱感應複寫紙;美國影印(American Photocopy)於一九五二年推出的岱爾美自動黑白複印機(Dial-A-Matic Autostat),以一般攝影術的改良版為基礎提供複印功能;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於一九五三年推出的維利費(Verifax)三合一多功能複印機,使用一種稱為染料轉印法(dye transfer)的技術,諸如此類。但與迪克先生的油印機不同的是,這些產品幾乎立即都有了現成市場,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市場確有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產品與它們的功能,能讓使用者產生一種強而有力的心理迷戀──現在看來,情況似乎果真如此。在社會學者永遠指為「廣眾」(mass)的社會,將一件獨一無二的東西複製成數量眾多的東西,總是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概念。
不過,這所有草創初期的複印機,都有嚴重得讓人卻步、揮之不去的缺陷。舉例來說,岱爾美與維利費難以操作,而且複印出的文件是濕的,需要晾乾;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的熱感複印機若熱度過高,複印出來的文件會變黑;此外,這三種複印機都必須使用製造廠提供、經過特殊處理的紙張。要將「文件複印」這種難以抗拒的概念綻放為一種爭相效尤的狂潮,還需要一項科技突破,而這項科技突破於一九五○年代將結束時,隨著一種新機器的問世而出現了。這種新機器運用一種叫做「靜電複印」(xerography)的新原則,能夠使用一般紙張製作乾的、高品質的永久性複印文件,而且操作也簡便得多。
這種新機器一經推出,效果立即燎原。主要由於靜電複印技術的運用,據估全美境內每年製作的複印文件(不是複寫)的件數,從一九五○年代中期的約兩千萬份,爆漲到一九六四年的九十五億份,再到一九六六年的一百四十億份──這還不包括歐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境內數以億計的複印文件。不僅如此,教育人員對印製教材、商人對通訊文件的態度,也出現很大的改變。前衛思想家開始對靜電複印技術讚不絕口,說它是一項革命,重要性媲美車輪的發明。只要投幣就能操作的複印機,開始在賣糖果的小店與美容院出現。狂潮──沒有十七世紀突然爆發在荷蘭的鬱金香狂潮那麼狂,但影響力大概比鬱金香深遠得多──已經全面展開。
一九六○年代美國最輝煌的商業成功
造成這場大突破的公司,當然正是紐約州羅徹斯特市(Rochester)的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這幾十億、幾百億複印文件使用的機器,大部分都是全錄的產品,因此全錄也成為一九六○年代最輝煌的商業成功。一九五九年,當時稱為哈洛伊德全錄(Haloid Xerox, Inc.)的這家公司,推出第一部自動靜電複印辦公室複印機,創下三千三百萬美元的銷售業績。一九六一年,它的銷售業績為六千六百萬美元,到一九六三年高達一億七千六百萬,到一九六六年超過五億美元。當時,該公司的執行長喬瑟夫‧威爾森(Joseph C. Wilson)指出,如果業績繼續這樣成長下去(也許,對每個人來說都幸運的是,這種事不大可能發生),二十年後全錄的業績將比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還要大。
在《財星》(Fortune)雜誌一九六一年全美五百大企業還榜上無名的全錄,在一九六四年排名第二二七,在一九六七年攀升到第一二六名。《財星》雜誌的排名以年度銷售額為估算基礎,若以某些其他標準來算,全錄的排名遠比第一七一名高得多。舉例來說,在一九六六年初,以淨利而論,它排名全美約第六十三位,若根據銷售利潤比,它可能名列第九。若以股票市值而言,全錄這家新秀的排名約為全美第十五位,比美國鋼鐵、克萊斯勒、寶鹼(Procter & Gamble)與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這些老牌大廠還要高。投資大眾對全錄的熱情追捧,讓它成為一九六○年代股市的「葛康達」(Golconda),那是一座印度古都,曾以出產巨型鑽石而聞名。任何人若在一九五九年年底買進全錄股票抱著不放,直到一九六七年初再脫手,會發現自己的投資賺了六十六倍。任何人若能超級洞燭機先,能在一九五五年就買進哈洛伊德的股票,他的原始投資會幾近於奇蹟也似,成長一八○倍。全錄的成功,造就了一批所謂的「全錄百萬富翁」,自也不足為奇。這批富翁共有七百人,大多數住在羅徹斯特地區,或者來自這個地區。
就像哈洛伊德公司創辦人之一的老喬瑟夫‧威爾森,是前文所述那位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間擔任全錄公司老闆的小喬瑟夫‧威爾森的祖父一樣,一九○六年在羅徹斯特成立的哈洛伊德公司,也是全錄公司的祖父級前身。哈洛伊德公司製造攝影感光紙,就像所有攝影業者一樣,尤其是那些位在羅徹斯特的公司,它生活在近鄰伊士曼柯達的巨型身影下。但即使是在這種陰影的壓制下,哈洛伊德仍能以還不錯的成績撐過大蕭條。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那幾年,競爭與勞工成本雙雙增加,迫使該公司搜尋新產品,該公司旗下的科學家當時發現,俄亥俄州哥倫布城(Columbus)非營利工業研究組織巴特爾紀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正在研究的一種複印程序似乎很有可為。
說到這裡,故事得拉回一九三八年,地點在紐約市皇后區艾斯特利亞(Astoria)一間酒吧樓上的廚房。當時三十二歲、名不見經傳的發明人契斯特‧卡爾森(Chester F. Carlson),就用這間廚房充做實驗室來進行研究。卡爾森的父親是祖籍瑞典的理髮師,卡爾森在從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物理系畢業以後,便進入P.R.馬洛里公司(P. R. Mallory & Co.)設在紐約的專利部門工作,馬洛里公司是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一家電氣與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者。為了追求名利與獨立,卡爾森將公餘之暇全力投入辦公室複印機的發明工作,還聘了一位名叫奧圖‧康奈(Otto Kornei)的德國難民物理學者做幫手。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用了一堆笨重的裝備、造了陣陣煙霧與臭氣之後,他們的實驗有了成果,能夠將「10-22-38艾斯特利亞」這幾個不起眼的字,從一張紙傳到另一張紙上。
這項被卡爾森稱為「電子攝影」(electrophotography)的程序,有五個基本步驟:在紙張上充上靜電(例如用毛皮磨擦紙面),以增加紙面的感光度;將這個紙面置於一頁寫了字的文件前,形成一種靜電形象;在紙面撒上一種只會黏附在充電地區的粉,形成潛在形象;將這形象轉移到一種紙上;最後,加熱以固定形象。這些步驟的每一步本身,與其他技術都有相當關係,算不上新,但結合在一起卻產生前所未見的效果──事實上,正因為它過於新奇,當年那些商業鉅子與重量級人士,在隔了很久以後,才逐漸發現這套新技術的潛能。卡爾森利用他在紐約市區馬洛里公司專利部門學得的知識,立即建了一套複雜的專利網絡保護這項發明,並且展開兜售──康奈不久後便離開了、另有高就,就此永遠離開電子攝影這一行。之後五年間,卡爾森一面在馬洛里工作,一面透過一種新形式向國內各大辦公室裝備公司提供這項程序的專利權,以拓展他的第二產業,但每一次都被打了回票。最後,在一九四四年,卡爾森說服巴特爾紀念研究所針對他這項程序展開進一步研發,並且言定新程序一旦出售或以授權方式出讓,權利金的四分之三歸巴特爾研究所所有。
於是,靜電複印術就這樣問世。書歸正傳,到一九四六年,巴特爾研究所對卡爾森這項程序的研究,已經引起哈洛伊德公司好幾個人的注意,其中包括即將接掌公司的小喬瑟夫‧威爾森。威爾森與他新結交的一位友人索爾‧利諾維茲(Sol M. Linowitz)談起這件事。利諾維茲剛從海軍退役不久,是一位聰明、有活力、關心公共事務的青年律師。當時,他忙著在羅徹斯特籌備一家新電台,準備播放自由派觀點,與當地甘奈特(Gannett)報系的保守派言論打對台。哈洛伊德公司雖有自己的律師,但威爾森對利諾維茲的能力激賞不已,於是請利諾維茲替哈洛伊德「專案」負責巴特爾這個案子。利諾維茲後來說:「我們前往哥倫布城,看研究人員用貓皮磨擦一片金屬。」經過多次參訪,雙方達成協議,哈洛伊德同意與巴特爾一起進行研發、分攤研發成本,從而取得卡爾森這項程序的使用權,卡爾森與巴特爾則可以取得權利金。其他一切似乎都因這項協議應運而生。一九四八年,在為卡爾森這項程序尋找新名稱的過程中,一名巴特爾的研究人員找上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一位古典文學教授,兩人將兩個古希臘文字結合在一起,造出「xerography」這個字,直譯為「乾的書寫」(dry writing)。
另一方面,巴特爾與哈洛伊德的小型科學家研究團隊,在這項程序的研發過程中,碰上一個又一個令人困惑、始料未及的技術難題。曾有一段時間,由於哈洛伊德的研究人員實在心灰意冷,想乾脆把靜電複印技術專利權賣給IBM。但這念頭最後取消了,研究工作繼續進行,成本也逐日升高,哈洛伊德對這項程序的承諾,也逐漸成為一種「不成功就成仁」的要務。一九五五年,新協議簽訂。根據這項新協議,哈洛伊德擁有卡爾森的全部專利,負擔研發計劃的全部成本。為了支付這些成本,哈洛伊德發行巨額股票給巴特爾,巴特爾則將其中一小部分交給卡爾森。這項計劃的研發成本極為驚人;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六○年間,哈洛伊德在靜電複印技術上花了大約七千五百萬美元,這個金額大約相當於它在同期間例行營業額的兩倍。為了補足差額,哈洛伊德一面舉債,一面發行普通股籌資,賣給那些好心人士、那些敢於冒險,或那些生成慧眼能夠預知未來的人。部分也因為不忍眼見本地公司陷於困境,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也買了哈洛伊德巨額籌資基金,這些股票的買進價格由於之後除權,約為每股○‧五美元。羅徹斯特大學一位官員還憂心忡忡地警告威爾森:「如果兩、三年以後,我們為了停損,不得不出脫手中的哈洛伊德股票,請不要生我們的氣。」威爾森向他保證,絕不生氣。
為了支持公司度過難關,威爾森與公司其他幾位主管,在領取薪酬時,除了小部分現金以外,大部分領的是公司股票。有幾位主管甚至拿出自己的積蓄,將房子抵押來支持公司。(在這些主管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利諾維茲。事實證明,他與哈洛伊德的合作一點也不是專案關係;他成為威爾森的左右手,負責公司至關緊要的專利事務,負責組織與指導公司的國際加盟業務,後來還做了一任公司董事長。)一九五八年,儘管使用靜電複印技術的重大產品還沒有上市,公司經過仔細考慮,改名為哈洛伊德全錄。公司使用的註冊商標,是哈洛伊德早幾年已經採用的「XeroX」──威爾森也承認,當年採用這個商標,完完全全就是模仿伊士曼柯達的商標「Kodak」。最後,「XeroX」商標中那個大寫字母「X」沒多久就降了一級,成為小寫的「x」,因為大家都懶得下工夫將最後那個字母改成大寫。不過,這個像「Kodak」一樣,幾乎是標準迴文(順著唸與倒著唸都一樣)的商標一直沒有變。威爾森說,公司許多顧問曾經極力反對「XeroX」或「Xerox」這個商標,他們擔心民眾不知道該怎麼唸這個字,也擔心民眾可能認為它代表一種防凍劑,更擔心這個商標會讓重視財務的人想到一個非常喪氣的字:「zero」(零)。
然後到一九六○年,大爆炸出現,突然一切事情完全反轉。過去擔心商標名字取得不好,現在公司擔心的是這名字太好了,因為無論在談話、在印刷文件中,「to xerox」(去複印)這個新動詞開始頻繁出現。頻繁的程度甚至已經威脅到公司的專利權益,迫使全錄展開一項精心策劃的行動,以制止這種濫用情事。﹝(一九六一年,哈洛伊德全錄公司索性把名字改為簡單的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全錄的主管過去為自己與家人的前途擔心,現在他們擔心自己會被一些親友們罵得狗血淋頭,因為當公司前景堪虞、股票只值○‧二美元一股的時候,這些主管曾經力勸親友們「不要買」公司的股票。簡言之,只要擁有一堆全錄股票的人,包括那些領股票不領現金、為公司省錢的主管,也包括羅徹斯特大學與巴特爾紀念研究所那些好心人,都成了富翁,或者富上加富。與全錄訂了好幾次約、得到許多股票的卡爾森,在一九六八年擁有的全錄股票市值好幾百萬美元,並因此成為全美第六十六名最有錢的人(根據《財星》雜誌的排名)。
社會企業先驅
這就是全錄發跡的簡史,它有一種老式的、甚至是十九世紀的味道:發明家形單影隻地在簡陋的實驗室中奮鬥,小小的家庭式公司,草創初期的挫敗,對專利系統的依賴,用古典希臘文找商標名,最後高奏凱歌、彰顯自由企業系統。不過,全錄的故事還有另一層意義;它不僅重視身為一家企業對股東、員工與顧客的責任,還進一步強調對社會整體的責任。就這一層意義而言,它不僅與大多數十九世紀的公司大不相同,事實上還走在二十世紀公司風氣之先。威爾森曾說:「訂定崇高目標,擁有幾乎不可能達到的抱負,讓人充滿有志竟成的信心──這些事像損益表一樣重要,或許還更重要。」其他的全錄主管也經常極力強調所謂的「全錄精神」,說這不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人類為了謀求本身福祉而強調「人性價值」的事。大公司像這樣使用美麗詞藻、語出驚人的狀況所在多有,所以全錄的主管說這樣的話,當然也一樣啟人疑竇,而且有鑒於該公司獲利之豐,這些說法聽來甚至讓人刺耳。但有證據顯示,全錄這些話並不是說著好聽的。
在一九六五年,該公司捐了一百六十三萬兩千五百四十八美元給教育與慈善機構,一九六六年也捐了兩百二十四萬六千美元;在這兩年中,獲利最大的都是羅徹斯特大學與羅徹斯特社區福利基金(Rochester Community Chest),而且在這兩年,該公司的捐款還相當於稅前淨利約一‧五%。與大多數其他大公司投入慈善的經費相比,這個百分比要高得多。舉例來說,美國無線電公司與AT&T都以樂善好施著名,但美國無線電公司在一九六五年捐助的善款總額,只占同年稅前收益約○‧七%,而AT&T的捐助比重也比一%少得多。為了宣示它對社會公益的堅持,全錄並在一九六六年投入「一%計劃」,即一般所稱的「克利夫蘭計劃」(Cleveland Plan),這是成立於克利夫蘭的一項專案,參加專案的地方企業同意,除了其他慈善捐助以外,每年以稅前營收的一%捐助地方教育機構,也因此只要全錄的營收持續增加,羅徹斯特大學與當地其他教育機構,面對未來都能有所保障。
在其他問題上,全錄也願意為了與獲利無關的理由而冒險。威爾森在一九六四年一篇演說中表示:「公司不能拒絕在大眾關切的重大議題上採取立場。」這種說法在商場上簡直就是異端邪說,因為在公共議題上採取立場,幾乎等於是在自絕於反對這些立場的客戶與潛在客戶。當時全錄採取的主要公共立場就是支持聯合國,也因此開罪了反對聯合國的人。一九六四年初,全錄決定以一整年的廣告預算四百萬美元,為一系列探討聯合國的電視網節目背書,這些節目在播出時不帶廣告,也不播任何全錄公司的標誌,只在每一個節目的開始與結尾附上一段聲明,說明這是全錄付費的節目。
那一年七月與八月,在全錄宣布這項支持聯合國的決定之後約三個月,反對這系列節目的信件彷彿雪片飛來,要求全錄撒手。這些信件總計約達一萬五千封,有的以溫言好語相勸,有的口氣強硬,形同開罵。其中許多信說,聯合國是用來剝奪美國人憲法權益的工具,聯合國憲章部分是由美國共產黨草擬的。還有幾封來自公司負責人的信,更揚言除非取消這個系列節目,否則他們的辦公室將不使用全錄的機器。只有少數幾封信的發信人提到激進右派反共組織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而且沒有一個人表明自己是這個協會的一員。不過,相關證據顯示,這項信件攻勢是該協會精心策劃的行動,它不久前曾發表刊物,呼籲會員寫信給全錄,抗議這項聯合國系列節目,還說發動潮水一般的信件攻勢,曾使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從飛機上除下聯合國標誌。
之後全錄展開調查,經過分析後發現,這一萬五千封信出自約四千人手筆,進一步證明這是一次有系統的行動。但無論怎麼說,全錄主管與董事並沒有被這些信件說服,也沒有被它們嚇到。聯合國系列節目於一九六五年出現在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電視網,而且廣獲好評。威爾森後來說,這個節目與不理會抗議、堅持播出的決定,雖然為全錄樹立了一些敵人,但因此交到的友人要多得太多。許多觀察家認為,從威爾森就這件事發表的多項公開聲明判斷,威爾森不僅具有優異的商業判斷能力,還有一種甚為罕見的商業浪漫色彩。
市場漸趨飽和,開始多角化經營
一九六六年秋季,全錄開始遭到推出靜電複印技術以來的第一波背運。此時,辦公室複印機這一行有四十幾家業者,其中許多業者在全錄的授權下生產靜電複印裝置。﹝全錄唯一不肯授權的,是一種叫做硒鼓(selenium drum)的技術,它能讓全錄的複印機在一般紙張上進行複印。所有與全錄競爭的產品,都仍然必須使用經過處理的特殊紙張。﹞全錄一直享有搶先進入新市場的業者所享有的那種優勢,也就是能夠收取高價。財經周刊《巴倫》(Barron's)在八月間指出:「就像所有科技發展必須面對的宿命一樣,這項曾經風光一時的發明,可能很快就會成為一種不足為奇的司空見慣之事。」標榜低價的新業者成群湧進複印市場;一家公司在五月間一封致股東的信中預料,不久會有十美元或二十美元一台的「玩具」複印機上市(一九六八年真有這麼一種玩具複印機上市,售價約三十美元),甚至有人說,有一天,商家會為了促銷紙張而免費贈送複印機,就像業者為了促銷刀片而贈送刮鬍刀一樣。
全錄了解自己的這些專利壟斷總有一天要成為公共財,幾年來也不斷購併主要包括出版與教育等其他領域的公司,以拓展營運觸角。舉例來說,它在一九六二年收購大學微縮膠片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一座未發行手稿的微縮膠片圖書館、絕版書、博士論文、期刊與報紙。在一九六五年,它開始購進另外兩家公司:一是美國教育出版公司(American Education Publications),全美最大的中小學教育期刊出版公司;另一是基本系統(Basic Systems),一家教學器材製造業者。不過,這些行動未能扭轉市場對全錄的成見,全錄的股價開始重挫。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它的股價還有二六七又四分之三美元,到十月初只剩下一三一又八分之五美元,公司市值腰斬還不止。從十月三日到十月七日單一交易週內,全錄跌了四二‧五點;特別是在十月六日這一天,紐約證交所不得不將全錄股票的交易暫停五小時,因為這一天有價值大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全錄股票求售,但一張買單也沒有。
九一四:史上第一部最成功,也最有個性的複印機
我發現,公司在經歷挫折時的表現最值得注意,於是選了一九六六年秋季這段期間,對全錄與它的員工進行觀察──我想做這件事,已經想了約有一年。一開始,我先熟悉它的產品──到了一九六六年,全錄的複印機系列與相關產品已經琳瑯滿目。舉例來說,有一種與辦公桌一般大小的九一四型複印機,無論什麼頁面,包括印刷、手稿、打字稿或畫圖等,都能製成黑白複印,但頁面大小不得超過九×十四吋,每複印一份需要約六秒鐘;八一三型的體積小得多,可以擺在辦公桌上,基本上就是一種九一四的縮小版(套用全錄技術人員的話說,就是「放了氣的九一四」);二四○○型是一種高速複印機,與現代廚房的爐灶一般大小,每分鐘可以複印四十份,一小時能複印兩千四百份;複印流(Copyflo)機型能將微縮膠片放大為書本一樣大小的一般頁面,然後複印;LDX能將文件透過電話線、微波無線電或同軸電纜傳輸;還有由美格福斯(Magnavox)設計、製造,但由全錄經銷的電傳傳真機(Telecopier),它有點像是LDX的初級版,只是一個小盒子,使用者只須把小盒子裝在一般電話機上,就能迅速將一張照片傳給另一位也在電話機上裝了這種小盒子的使用者,因此甚獲外行人的青睞(不過傳的時候,發出的噪音也著實不小。)然而,對全錄及它的客戶來說,在這所有的裝置中,第一種劃時代性的自動靜電複印機九一四仍是最重要的產品。
有人認為,九一四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商業產品,但這項說法既不能證實也無法否認,其中一個原因是全錄不發表公司個別產品的確切營利數字。不過,全錄確實曾經表示,在一九六五年,九一四占全錄總營收約六二%,而全錄在這一年的總營收為兩億四千三百萬美元。在一九六六年,一部九一四的售價為兩萬七千五百美元,也可以用二十五美元的月租,外加至少四十九美元的複印費用(每複印一頁○‧○四美元)來租一部九一四。這樣的收費經過精心安排,讓租用比買划算,因為最後總結起來,全錄靠出租所賺的錢比賣機器所賺的錢還多。
漆成象牙白色的九一四,重達六百五十磅,看起來很像一個摩登的L型金屬辦公桌。需要複印的東西──可以是一張紙、一本打開的書本的跨頁,或甚至是手錶或獎章這類小型立體物件──只要面朝下、擺在平滑表面的玻璃窗上,再按一個鈕,九秒鐘以後,複製出的頁面就會跑進一個文件盤裡,一個類似「發文籃」的地方。就技術角度而言,由於九一四過於複雜(全錄有些推銷員說,它比汽車還複雜),所以很容易出毛病,因此全錄養了一批為數幾千人、理論上可以隨傳隨到的修護大軍。
九一四最常見的毛病是複印紙夾紙,全錄替這個毛病取了一個很有畫面感的名字叫做「mispuff」(噴氣定位錯誤),因為每張紙都要先經機器內部「puff」(噴出)的氣提升到定位,才能進行複印,一旦「puff」的過程「miss」(出了差錯),機器就無法運作。有時噴氣定位錯誤的情況嚴重,紙張接觸到機器內的高熱零組件,機器還會因此冒出令人害怕的白煙。全錄建議,如果遇到這類狀況,頂多只須使用附在機器旁的小型滅火器就可以了,因為如果不予理會,火會自行熄滅,不會造成什麼傷害。但如果拿一桶水澆向九一四,卻可能將也許會致命的電伏傳到它的金屬表面上。除了故障問題以外,九一四還需要負責操作的作業員細心關照,這些作業員幾乎都是女性。﹝早期負責打字機(typewriter)操作的女性,本身就叫做「typewriter」,好在沒有人把操作全錄複印機(Xerox)的女性也叫做「xeroxes」。﹞
九一四的複印紙與稱做「toner」(調色粉)的黑色靜電粉必須定期更新,而它最重要的零組件──那個硒鼓,必須用一種不會造成刮痕的特製棉布定期清拭,而且得經常上臘保養。我曾經與一部九一四及它的作業員共處了幾個下午,見證了我生平僅見、一位女性與一件辦公室裝備之間最親密的關係。操作打字機或電話接線總機的女性,對她使用的裝備不會有興趣,因為這些裝備沒什麼神奇之處;操作電腦的女性,對電腦也只會感到厭煩而已,因為電腦讓她完全無法理解。但九一四有獨特的動物屬性:妳必須餵它,必須奉承它;它有時讓人膽戰心驚,但有時也很溫良馴服;它可能突如其來地幹一些壞事,但一般而言,妳對它好,它也會對妳好。我觀察的這位作業員對我說:「一開始,我很怕它。全錄的人說:『如果妳怕它,它就不會好好工作。』這話說得真不錯,它是個好東西。我現在喜歡它了。」
複印的多種用途,以及可能爭議
我和全錄的一些銷售代表談過話,知道他們不斷想著運用公司產品的新點子,卻一再發現民眾想出的點子領先他們太多。其中一個稀奇的點子,還能讓新娘如願以償、得到她的婚禮禮物。這一招是這麼用的:準新娘寫一份最想要的禮物清單,交給一家百貨公司,百貨公司把這份清單送到它的新娘登記櫃台,櫃台裡裝了一部全錄複印機。新娘的友人經通風報信來到這個櫃台,領到一份清單拷貝。接著,這友人在百貨公司選購完畢,劃去拷貝單上他已經備妥的禮物,再把拷貝單交還給櫃台。於是,櫃台修訂清單,準備新娘下一位友人前來購物。看來,希臘神話中專司婚姻的海曼神(Hymen),魅力真是勢不可當!
另一方面,紐奧良與其他許多地方的警察局,在為送進拘留所的人犯開立私人物品清單時,也不再費時耗力地打字了。他們把人犯的錢包、手錶、鑰匙之類的隨身小東西擺在九一四的掃描玻璃窗上,只需要幾秒鐘,一張照相影本收據就完成了!醫院用靜電複印機器來複印心電圖與實驗室報告,券商也可以更快將一些熱門消息通報給客戶。事實上,任何人只要想得出利用複印機的新點子,都可以隨便走進一家設有投幣式複印機的雪茄菸店或文具店,做他想做的事。(有趣的是,全錄生產了兩種規格的投幣型九一四,一種投幣單位為一角美元硬幣,另一種為二十五分美元硬幣,供購買或租用這些機器的店家選用。)
不過,複印也遭到濫用,而且情況顯然嚴重;最明顯的一種濫用現象,就是過度複印。這種現象在官僚體系中尤其普遍──明明只需要複印一份就夠了,卻想複印兩份或更多,根本無須複印也想複印一份等。一度用來代表官僚浪費的「in triplicate」(製作三份)這個詞,實在過於輕描淡寫,不足以說明情況的嚴重。只需要按一下按鈕,機器就會展開一連串行動,乾淨俐落地將複印成果放進文件匣──這一切都讓人有一種飄飄欲仙之感,初次使用複印機的人也總是想將什麼都複印。此外,一旦使用過一次複印機,很容易讓人上癮。或許,這種複印成癮的毛病最危險的地方,不在於檔案愈建愈多、反而埋葬了重要資料,而在於對原始文件的一種逐漸萌生的負面態度──許多人開始認為,一份文件除非經過複印,或者本身是一份複印文件,否則不是重要文件。
靜電複印術帶來的一個比較立即性的問題是,它帶來一種違反著作權法的極大誘惑。全美各地所有大型公立與大學圖書館──以及許多中學圖書館──此時都已經設有複印機,教師和學生如果需要從一本書裡找幾首詩、從一本選集裡找某篇短篇小說,或是從一本學術期刊當中找一篇論文的話,只需要從圖書館的書架上取下這本書,再拿到圖書館的複印室複印就好,需要幾份就用全錄複印機複製幾份。這麼做的結果,當然影響到作者與出版商的收益。這種著作權侵權情況究竟有多嚴重,並無法律紀錄可尋,或許只因為出版商與作者不知道有這種侵權情事;更何況,這些辦教育的人本身往往也不知道他們這麼做有任何不法。
幾年前,一個教育家委員會向全美各地教師發出通告,說明教師們有權或無權複印哪些材料。通告發出之後,教育家向出版商要求複印許可的事例大幅增加。此次事件間接顯示,在靜電複印術普及之後,許多人已經犯下著作權侵權情事而不自知。此外,還有一些更具體的證據,也可以說明當時的狀況;舉例來說,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圖書館系所一名職員在一九六五年公開指出,圖書館預算有九○%花在員工薪酬、電話、複印與電傳之類的事務,花在書籍與雜誌上的錢只占十%。
在某種程度上,圖書館也想自行負起著作權的保護工作。以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主館的影印服務為例(每週都要處理約一千五百件圖書館資料複印申請),就曾經發出通告,要求複印的人「有著作權保護的材料,只能在『合理使用』的限度內複印;所謂『合理使用』的意思就是,複印數量與類型大體而言只限於摘要節錄,屬於法有先例、不構成侵權行為者。」通告中並且指出:「一切因複印,以及之後因使用複印文件而可能產生的問題,應由複印申請人負全責。」紐約公共圖書館在這篇聲明的第一段,似乎表示它願意負起著作權保護工作,但在第二段卻把這項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這種模稜兩可,或許可以反映當時圖書館複印機使用者廣泛的不安感。
不過,一旦出了圖書館門外,這種不安往往也不見蹤影。一般而言非常守法的商人,似乎將著作權侵權行為當成隨意穿越馬路一樣,不以為意。我聽說有這麼一回事:一位作家在應邀出席一場商界領導人研討會時,駭然發現自己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裡有一章遭到複印,拷貝的副本散發給與會者,作為研討會的討論基礎。這位作家於是提出抗議,但主事的商人不僅大感驚訝,甚至覺得這位作家傷了他們,因為他們覺得複印他的文章,正表示他們對他的重視,所以這位作家應該感到高興才是。不過當然,這行徑就好像一個賊在偷了一位女士的珠寶以後,還在這位女士面前展示這件珠寶,稱讚它有多美一樣。
著作權保衛戰
有論者認為,目前為止發生的這些事,只是一種圖象革命的第一階段。加拿大哲人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在《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季刊一九六六年的春季刊中寫道:「靜電複印術正為出版世界帶來一場恐怖統治,因為它意味著每位讀者都可以既是作者也是發行人。在靜電複印術的支配下,著作與閱讀都成為生產導向……靜電複印術是對印刷術世界的電氣入侵,它代表一場出現在這個老領域的全面革命。」儘管麥克魯漢時而反覆(他曾經承認:「我每天都在改變主意」),但此話言之成理。雜誌上也出現各式各樣的文章,預言書籍有一天將走進歷史,未來的圖書館會是一種像怪獸般的電腦,能夠透過電子與靜電複印科技儲存、檢索書本的內容。在這樣的圖書館裡,「書籍」只是一個個細小的「一版」電腦膠卷晶片。雖然每個人都同意,這樣一種圖書館在短期內還不可能出現,但一些謹慎的出版商沒隔多久,已經有了未雨綢繆的反應。﹝從一九六六年的年底起,哈考特─布雷斯與世界圖書公司(Harcourt, Brace & World)出版的所有圖書,將版權頁上行之多年的「版權所有」那一行老字,加注了一段唸起來令人有點害怕的文字:「版權所有。這本刊物的任何一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手段,無論是電子或機械,包括影印、記錄或任何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進行重製或傳輸。」而其他出版商也立即跟進。﹞
一九六○年代末期,全錄旗下的大學微縮膠片公司,也採取了版權保護措施。大學微縮膠片當時為顧客提供放大絕版書微縮膠片、印製成精美平裝書的服務,每頁收費○‧○四美元;如果是複製有版權的書,公司會根據複製份數提供作者版稅。然而,幾乎任何人都能以低於市價的成本、自己複製一本書,已經不再是幾年以後的夢想,而是既已成真的事實。業餘出版人只須準備一台小型膠印機,而且能夠使用全錄複印機就行了。靜電複印術一項次要、但仍然重要的特性,是它能夠製作膠印使用的主版頁,而且製作時間與成本比過去少得多。據美國作家聯盟的顧問厄文‧卡普(Irwin Karp)指出,在一九六七年,將這兩項技術結合在一起使用,只需要幾分鐘時間就能以一頁○‧○○八美元的成本「發行」(裝訂費另計)一版五十本印刷書籍;如果一版的數量更大,成本也就更低。一位教師如果想將市價每本三‧七五美元、共六十四頁的詩集複印五十本,發給班上五十名學生,只要決心不理會版權法,也可以用每本略多於○‧五美元的低成本做到這件事。
作家與出版商都同意,這種新科技帶來的危險在於,一旦書本走入歷史,作家與出版商、最後連寫作本身也將走入歷史。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社長小赫伯特‧貝利(Herbert S. Bailey, Jr.),在《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中寫道,他的一位學者友人已經取消訂閱一切學術期刊,每天只是泡在公共圖書館裡掃描這些期刊的內容,找出有意閱讀的文章進行複印。貝利說:「如果所有學者都這麼做,這世上將沒有學術性雜誌。」自一九六○年代中期起,美國國會已經開始考慮修訂著作權法,而這是自一九○九年以來的頭一遭。在聽證會進行期間,一個代表美國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與一群其他教育團體的委員會,強而有力地指出,美國如果要讓教育跟上國家成長的腳步,就必須針對學術性用途,將現有著作權法與「合理使用」法則自由化。毫不令人意外,作家與出版商當然反對這種自由化,他們堅持現有著作權法已經對他們的生計形成傷害,日後隨著靜電複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對他們生計的危害只會變本加厲。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在一九六七年通過的一項法案,明文宣示「合理使用」法則,而且不提教育性複印豁免,似乎是代表作家與出版商的一項勝利。不過,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這場鬥爭的最後勝負仍然未定。麥克魯漢深信,維持既有著作權保護的一切形式都是走回頭路的思考,必將失敗無疑。至少他在寫下列這篇刊在《美國學者》的論文時,如此深信。他在論文中表示:「除了運用科技手段,想保護自己、不受科技之害是不可能的。一旦你運用某一階段的科技創造了一種新環境,就必須運用下一階段的科技才能創造一種反環境。」但作家一般不擅長科技,而且很可能在反環境中也發達不起來。
為了應付公司產品打開的「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面對這些爭議,全錄的作為似乎頗能謹守威爾森訂定的崇高理念。儘管就商業利益角度而言,全錄理應鼓勵人們複印,複印得愈多愈好,至少也不會勸人少複印;但事實是,全錄花費相當工夫向全錄複印機使用者說明他們的法律責任。舉例來說,每一部新機器在交到客戶手上時都會附上一塊紙牌,明列一長串不能複印的東西,其中包括紙幣、政府債券、郵票、護照與「非經著作權所有人允許的任何形式或類型的著作權材料。」(至於有多少這種紙牌被使用者丟進垃圾桶,則是另一個問題。)此外,在著作權法修訂爭奪戰中夾在中間的全錄,始終能夠抗拒乘機大發利市的誘惑,擔任樹立社會責任感的表率──至少就作家與出版商的觀點而言是這樣的。
相形之下,複印業者大體上或保持中立,或倒向教育家這一邊。在一九六三年的一項著作權法修正案研討會中,一名業界發言人甚至辯稱,學者使用機器複印,不過是將親手複寫加以簡便延伸罷了,而親手複寫傳統上都是公認合法的。不過,全錄並沒有這麼做。一九六五年九月,威爾森寫信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毫無遮掩地反對新法律提供任何類型的複印免責權。當然,在評估這種似乎是唐吉訶德式立場的過程中,我們應該不忘全錄既是一家複印機製造公司,也是一家出版公司;事實上,旗下擁有大學微縮膠片公司與美國教育出版公司的全錄,是全美最大的幾家出版公司之一。我從我的研究發現,傳統出版業者面對這家未來色彩濃厚的巨廠,難免有些迷惑徬徨;因為對他們來說,全錄不僅對他們熟悉的世界構成一項天外飛來的威脅,也是他們充滿熱情的同業與競爭對手。
實地參訪全錄,拜會公司大老
在對全錄的一些產品有了一些認識,對這些產品造成的社會衝擊做了一番思考之後,我前往羅徹斯特,一則累積與這家公司的第一手經驗,一則了解全錄的員工如何因應他們的物質面與道德面問題。在我前往羅徹斯特的時候,物質面問題顯然是當務之急,因為當時全錄股價一週跌了四二‧五點的慘劇記憶猶新。在前往羅徹斯特的飛機上,我讀著一份全錄最新的股東委託書複印文件,上面記著全錄每一位董事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持有的股票。為了打發時間,我算了一下幾位董事如果沒有出脫手中持股,在十月那個災情慘重的一週的帳面損失。舉例來說,董事長威爾森在二月持有十五萬四千零二十六普通股,所以他在那週虧了六百五十四萬六千一百零五美元。利諾維茲持有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六股,虧損一百四十九萬四千五百五十五美元。負責研發的執行副總約翰‧德紹(John H. Dessauer)持有七萬三千八百四十五股,所以應該損失了美金三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二元五角。就算是全錄的主管,這樣的損失也絕對不輕。既然如此,我在進入他們的公司以後,見到的會不會是一片愁雲慘霧,或至少是訝異、震驚?
全錄的主管辦公室位在羅徹斯特城中塔(Midtown Tower)的高樓層,底樓是室內購物中心城中廣場(Midtown Plaza)。(那一年稍後,全錄把總公司搬進對街的全錄廣場,廣場上有一棟三十層辦公樓、一座供民眾與公司使用的禮堂,還有一座大溜冰場。)在上樓前往全錄的辦公室以前,我在購物中心逛了兩圈,發現它有各式各樣的商店、一座咖啡廳、一些精品店、撞球場、種了一些樹、還有休閒座椅──儘管這裡氣氛極其平和而富足,但就像一些室外購物中心的休閒座椅一樣,也坐了一些流浪漢。這裡的樹由於缺乏陽光與空氣,顯得有些有氣無力,那些流浪漢看起來倒是滿有精神的。
搭乘電梯上樓以後,我見到事先約好的一位全錄公關,並且立即問他公司對這次股價暴跌一事的反應。他答道:「喔!沒有人太在意這件事。在高爾夫俱樂部,你會聽到許多有關它的輕描淡寫的談話。某人會對另一個人說:『今天你請喝酒,我的全錄昨天又虧了八萬塊。』威爾森對證交所那天被迫停止全錄交易的事,確實感到有些受傷,但除此之外,他的態度一直很從容。事實上,在不久前的一次聚會中,由於股票大跌,許多人圍著他,問他這是怎麼回事。威爾森當時回答:『嗯,你們知道,機會兩次來敲門,可是非常罕見的喔!』至於在辦公室裡,幾乎聽不到有人提這件事。」事實上,在進了全錄的辦公室以後,我真的沒聽到有關這件事的談話,而且事實證明他們這麼鎮定果然有理,因為才不過一個月多一點點以後,全錄股票大漲,不僅全面收復失地,不出幾個月以後還創下新高。
那天上午,我拜會了三位全錄科技專家,聽他們談起早年研發靜電複印術的故事。第一位與我會面的是德紹博士,就是一週前虧了三百萬美元的那一位。不過,我發現他的神色非常自在從容──我細想一下,這也合情合理,因為就算虧了這麼多,他手中的全錄股票仍然值九百五十萬美元以上。(幾個月以後,他的股票算一算價值不下兩千萬。)德紹博士在德國出生,是公司元老,自一九三八年起就主持公司的研發與工程部門,並且兼任副董事長。一九四五年,德紹在一份技術刊物中看到一篇有關卡爾森新發明的文章,於是第一個建議喬瑟夫‧威爾森注意這件事。我在他的辦公室牆壁上看到一張辦公室員工寫給他的賀卡,上面稱他是「魔法師」,我覺得他是一位笑容可掬、看起來很年輕的人,說話帶有一種剛剛可以通過魔法師鑑定考的口音。
德紹博士說:「你想聽我談一談往事,是嗎?嗯,它很刺激、很美好,但它同時也可怕得要命。有時我或多或少覺得自己就要發瘋了,是真的發瘋。錢一直就是個大問題。公司的運氣還算好,還有一些進帳,但也在危險邊緣。我們團隊的每一位成員,都在這項專案上下了大注。我連房子都抵押了,全身財產只剩下我的人壽保險。我已經賭上一切身家,沒有退路。我當時的感覺是,如果做垮了,威爾森與我都是商場敗將,但就我而言,我還多了一項科技敗將的罪名,這輩子沒有人還會給我工作。我也許得放棄科學,去做賣保險之類的工作了!」
德紹博士眼望天花板,以一種遙想當年的語氣說:「在那段早期歲月,幾乎沒有人對前途樂觀。我們自己很多人都曾經進來對我說,這鬼東西永遠做不成!最大的問題是,事實證明,靜電在高濕度環境中無法運作。幾乎所有專家都這麼說:『你永遠不可能在紐奧良搞複印。』而且就算真能做出複印機,行銷人員認為我們面對的潛在市場,充其量也不過只有幾千部複印機。有些顧問還對我們說,我們進行這項專案,根本就是腦子有問題。嗯,不過,你知道,結果一切都很圓滿──就連在紐奧良,九一四也運作得很好,而且市場很大。之後是桌上型的八一三,我再次賭上全部身家,堅持一種有些專家認為太脆弱的設計。」我問德紹,他是不是還在進行賭上身家的新研究,如果是,這項研究是不是像靜電複印一樣刺激?他回答:「你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是』,不過想進一步探討,就是專業知識的範疇了。」
科技突破,總是多少有點瞎打誤撞
我見到的第二位全錄主管是哈洛德‧克拉克博士(Harold E. Clark)。在德紹監督下直接負責靜電複印研發專案的他,對我說了許多當年卡爾森的發明怎麼整型、蛻變,終於成為一件商業產品的細節過程。克拉克博士是矮個子,說起話來很有專業風範。他原是物理學教授,在一九四九年加入哈洛伊德。他說:「契斯特‧卡爾森很像一位生物形態學家。」或許因為看到我面帶茫然,他淺笑了笑,繼續說道:「其實我也不知道『生物形態學家』究竟代表什麼,我想它的意思就是把一件事物與另一件事物合在一起,產生一件新事物。無論怎麼說,契斯特就是這樣的人。靜電複印在過去的科學研究工作中,絲毫沒有任何基礎。契斯特把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現象擺在一起,每個現象本身都艱澀難解,而且都是過去沒有人思考、連一點邊都沾不上的問題。結果就是攝影術本身問世以來,影像科技最大的突破。這還不說,他是在沒有任何有利的科學氣氛中做到的。你知道,科技史上出現過幾十件同步發現的先例,但像契斯特這樣的發現,根本就是絕無僅有。就像我第一次聽說一樣,直到現在,想到他的這些發現,仍然讓我稱奇不已。就一件發明來說,它非常了不起!唯一的問題是,就一件產品來說,它一點也不好。」
克拉克博士又笑了笑,繼續解釋說,轉捩點出現在巴特爾紀念研究所,而且就像科技突破的傳統一樣,多少是在瞎打誤撞的情況下產生的。主要問題出在卡爾森塗上一層硫的感光表面,它在經過幾次複印之後品質就會流失,不再有用。單純憑一種直覺,在沒有任何科學理論佐證的情況下,巴特爾的研究人員在感光表面加了少量硒。這是一種非金屬性元素,過去主要用在電阻器,也是一種使玻璃變紅的色素。硒與硫混合的表面,比純硫表面的效果好了一些,於是巴特爾研究員又加了一些硒。結果效果進一步改善,他們就這樣逐步增加硒的百分比,直到整個感光表面只有硒、沒有硫為止。這最後一種的表面效果最好,就這樣,他們用倒推的方式發現,硒──而且也只有硒──能讓靜電複印技術運作。
克拉克博士面帶沉思地說:「想想看,就是像地球近一百種元素之一的硒,這樣簡單的東西,這樣普通的東西就是關鍵。一旦發現它的效益,我們離成功已經不遠;不過,我們當時還不知道。我們到今天還擁有用硒進行靜電複印的專利,幾乎等於包辦了一種元素──怎麼樣,不錯吧?甚至到了今天,我們還不知道硒究竟是怎麼運作的。舉例來說,它沒有記憶效應,也就是說,過去的複印不會在鍍了一層硒的鼓上留下任何蹤跡。而且理論上說, 它似乎可以永遠做下去,不會壞,這項事實讓我們驚奇不已。在實驗室裡,鍍了一層硒的鼓可以經歷一百萬次複印,我們也不明白為什麼在做了一百萬次以後它開始效力降低。所以你可以看出,靜電複印的研發,大體上是一種觀察與實驗。我們是正規出身的科學家,不是東修西補搞發明的洋基客。不過,我們在東修西補與科學探討之間取得一種平衡。」
之後,我見到郝瑞斯‧貝克(Horace W. Becker),他是負責將九一四從工作模型階段推上生產線的全錄工程師。貝克來自紐約市布魯克林區,有一種把惱人的事說得頭頭是道的本領,他告訴我全錄九一四在推上生產線的這項過程中,遭遇到的令人寒毛倒豎的種種障礙與風險。當他在一九五八年加入哈洛伊德全錄的時候,他的實驗室設在羅徹斯特一家花園種子包裝店樓上,屋頂是漏的,每逢熱天,融化的焦油會從漏縫中滴下,濺在工程師與機器身上。到一九六○年初,九一四終於有了樣子,需要搬進座落櫻桃園街(Orchard Street)的另一間實驗室。貝克告訴我:「那也是一棟破舊的樓房,電梯動起來會發出嘎嘎聲響,旁邊還有一條鐵路,不時有滿載豬群的火車隆隆駛經。不過,我們有了自己需要的空間,而且屋頂也不會漏焦油下來。搬進櫻桃園街以後,我們的工作才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怎麼會這樣,我也說不明白。我們決定設立生產線的時機已到,每個人都忙得不亦樂乎。工會那些人暫時拋開他們的不滿,老闆們也忘了他們的考績問題。在這間實驗室,你分不清誰是工程師,誰是裝配工人。沒有人願意離開現場,週日裝配線關閉時,你溜進去一看,總會看到有人在調整什麼東西,或是在那裡閒逛,對我們的成果羨豔不已。換句話說,九一四終於就要問世了!」
貝克說,但機器在離開裝配線進入展示間、與客戶見面時,他的麻煩才剛開始,因為他現在負責故障與設計瑕疵問題。而就在民眾都睜大了眼看著它的時候,它演出一次全面大崩盤。九一四成了名副其實的愛德索:錯綜複雜的中繼設備不運作、彈簧斷裂、斷電,還有沒有經驗的使用者讓訂書針與迴紋針掉進機器,結果機器失靈(因此後來的每一部機器,都有一個防止訂書針掉落的袋子。)此外,潮濕、悶熱的天氣帶來可想而知的問題,還有高海拔地區帶來的一些始料未及的問題。貝克說:「總而言之,言而總之,當你按鈕時,這台機器有個什麼都不做的壞習慣。有時你按了鈕,它也做了一些事,但是做得不對。例如,當九一四第一次在倫敦舉行盛大公開展示時,威爾森親自出馬在儀式中按鈕。他按了鈕,結果不但沒有複印出任何東西,還把為機器供電的一部巨型發電機給燒掉了。」靜電複印就這樣在英國登場,有鑒於它這場處女秀的表現,以及之後英國成為九一四機型海外地區最大市場的事實,似乎不得不讓我們對全錄的彈性與英國人的耐性肅然起敬。
回饋鄉里,培養在地人才
那天下午,一位來自全錄公司的嚮導,開車帶我前往韋斯特(Webster)。韋斯特是一座農業城,位於安大略湖(Lake Ontario)湖濱,距離羅徹斯特只有幾哩路。我們來到貝克那座屋頂漏焦油的實驗室舊址,現在它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一座巨型現代工業園區,其中有一處占地約一百萬平方呎的廠房,所有全錄複印機都在這座廠房裝配(英國與日本分公司生產的機器除外),還有一處面積較小但似乎更精緻的研發單位。當我們參觀這座工業園區的生產線時,全錄嚮導向我解釋,這條生產線目前分成兩班,每天作業十六個小時,但它與其他幾條生產線的生產,好幾年來仍然供不應求。這名嚮導還告訴我,這座園區目前有近兩千名員工,而他們都是本地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的成員。之所以出現這種怪現象,主要是因為羅徹斯特原是一處成衣業中心,成衣業工人工會一直就是這個地區勢力最強的工會。
在我的嚮導把我送回羅徹斯特以後,我一個人展開行動,蒐集社區人士對全錄與它的成功的看法。我發現他們的看法很矛盾,比方說,有一位本地商人說:「全錄的存在對羅徹斯特來說,一直就是好事一件。當然,伊士曼柯達多年來都是這座城市的大頭領,而且仍是遙遙領先的本地最大企業,不過全錄現在位居第二,而且正在迅速趕上。面對這樣的競爭,對柯達不但沒有任何傷害,事實上還有很多好處。此外,本地出現成功的新公司,意味著新的金錢收益與新的就業機會。但是另一方面,這裡也有人痛恨全錄。本地的企業大多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紀,而他們對新來的人往往不是很友善。當全錄像流星一般竄起時,地方上有人心想它會像泡沫一樣幻滅──不,應該說他們希望它會幻滅。最重要的是,喬瑟夫‧威爾森與索爾‧利諾維茲一方面大談人性價值,一方面賺進大把鈔票的行事方式,也讓本地人有某種程度的反感。不過,怎麼說呢?這大概就是成功的代價吧!」
我來到位於金尼西河(Genesee River)河濱的羅徹斯特大學,訪問了校長亞蘭‧華里斯(W. Allen Wallis)。華里斯是個高個子,一頭紅髮,統計師出身,在伊士曼柯達等幾家在地公司擔任董事。其中伊士曼柯達一直就是羅徹斯特大學的聖誕老人,至今仍是它每年捐獻的最大施主。至於對全錄,這家大學也有幾個心生好感的好理由。首先,羅徹斯特大學投資全錄股票,資本利得約達一億美元,而且已經兌現賺了至少一千萬美元以上,它是全錄千萬富翁的典範。其次,全錄每年提供給它的現金贈禮之豐僅次於柯達,最近還響應羅徹斯特大學的集資,保證為它籌集近六百萬美元。第三,本身也是羅徹斯特大學畢業生的威爾森,自一九四九年起就擔任它的校董,自一九五九年起並出任它的董事長至今。華里斯校長說:「我在一九六二年來到這裡以前,從沒聽過公司會像柯達與全錄現在對我們這樣,對大學慷慨捐助。而他們寄望於我們的,只是要我們提供最高品質的教育,並沒有要我們為他們進行研究,或是做任何那一類的東西。當然,我們的科學研究人員與全錄的研發人員有許多非正式的技術顧問交流──與柯達、博士倫(Bausch & Lomb),以及其他公司的情況也一樣──但這不是他們支持這所大學的原因。他們希望讓羅徹斯特成為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因為他們需要人才。我們大學從未替全錄發明任何東西,我想永遠也不會有這種事。」
接班人就位,堅持理念是場持久戰
第二天上午,我在全錄主管辦公室會見全錄最高階非技術性領導人,最後一位是威爾森本人。我見到的第一位是利諾維茲,就是那位威爾森在一九四六年「暫時」找來幫忙,之後成為威爾森的左右手、一直留在全錄的律師。(全錄成名以後,社會大眾常以為利諾維茲在全錄不只是律師而已,他們常將他視為全錄的執行長。全錄的主管也知道這項普遍誤解,也不解何以會這樣,因為威爾森無論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之前擔任全錄總裁的期間,或是在之後擔任全錄董事長的期間,一直就是全錄的老闆。)我在利諾維茲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與他會了面,因為他剛奉命出任美國駐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大使,即將離開羅徹斯特與全錄,啟程前往華府履新。
利諾維茲五十來歲,顯得很有衝勁、很精明,而且很誠懇。首先他向我道歉,說他只有幾分鐘時間與我共處,隨即很快便說,依照他的看法,全錄的成功證明自由企業的老理念仍然有效。利諾維茲還說,全錄之所以成功,靠的是理想主義、堅持不懈、勇於冒險與熱情投入等幾項特質。說完這幾句話,他向我揮手道別,走出辦公室。我留在辦公室裡,覺得自己好像是留在火車月台、剛聽完一位候選人在競選列車後車廂發表演說的小城選民一樣,但如同許多這類選民,我也留下深刻印象。利諾維茲說的那幾句話儘管內容陳腐,但出自他的口中,卻不僅讓人覺得他說的是肺腑之言,還讓人覺得那幾句話是他發明的。我想,威爾森與全錄會想念他的。
彼得‧麥考洛克(C. Peter McColough)在威爾森出任董事長以後,繼任全錄總裁,而且顯然有一天會接班成為全錄的老闆(他在一九六八年成為老闆。)我看到他像關在籠中的野獸一樣,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還不時在一個高桌邊停下來寫幾個字,或是對著一台錄音機說幾句話。像利諾維茲一樣,麥考洛克也是一位自由派民主黨籍律師,不過他生在加拿大。他四十歲出頭,性格開朗、外向,許多人在談到他的時候,喜歡說他是新一代全錄人的代表,負有決定公司未來走向的重責大任。他終於停止踱步,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對我說道:「我面對成長的問題。」他接著說,想讓全錄在今後出現大規模成長,由於空間不夠,事實上有所不能,而且全錄採取的走向是教育科技。他談到電腦與教學機器,當他說他「夢想有一種系統,能用它在康乃狄克州寫下一些東西,不出幾個小時就能將這些東西複印,發送到全國各地的教室」時,我的感覺是,全錄的一些教育之夢很可能變成夢魘。不過,他接著又說:「精巧的硬體有一種危險,就是它讓人分神,無法全力投入教育。一個機器再精巧,如果你不知道用它來幹什麼,這機器又有何用?」
麥考洛克說,自他在一九五四年進入哈洛伊德以來,他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三間完全不同的公司──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是一家小公司,投入一場危險但刺激的賭博;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是一家成長中、享受勝利果實的公司;現在則是一家朝新方向進軍的巨型公司。我問他,他最喜歡的是其中哪一家公司,他沉思良久,終於回答:「我不知道。過去,我覺得工作時比較自由自在,也覺得公司裡每個人在勞工關係這類事務上都有共同看法。現在,我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壓力比過去大了,公司也變得更加沒有人味。我不能說日子比過去好過,也不能說日後可能會好過一些。」
在接待人員把我引進喬瑟夫‧威爾森的辦公室時,我頗感意外地發現,他的辦公室貼著老式的花草壁紙。統帥全錄大軍的這個人,竟有幾分多愁善感的神采?這似乎是讓我最吃驚的事。但他有一種坦然樸實、與人無爭的風範,與這壁紙搭配得很好。威爾森個頭不高,年近六旬,在接受我訪談的這段時間,他顯得很拘謹,態度幾近嚴肅,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多少帶一些猶豫。我問他,當年怎麼會進入家族企業,威爾森回答事實上他差一點沒有這麼做。他在大學主修的第二門課是英國文學,因此他也曾經考慮當個教師,或是在大學擔任財務與行政方面的工作。但在畢業以後,他進入哈佛商學院,成為班上成績最頂尖的學生,就這樣……無論怎麼說,他在離開哈佛那一年加入哈洛伊德,此時他臉上突然堆滿笑容,對我說,就是這樣有了今天。
威爾森最喜歡討論的主題,似乎就是全錄的非營利活動與他的公司責任理論。他說:「我們這種做法遭到某種怨懟。我的意思是,不僅有些股東感到不滿,說我們揮霍他們的錢──但是這種觀點站不住腳。在社區裡,雖然你未必會親耳聽到有人這麼說,但有時你憑直覺就能感覺得出他們在說:『這些年紀輕輕的暴發戶以為他們是誰啊?』」
我問他,那次寫信抗議聯合國電視網節目的事件,有沒有在公司內部造成任何擔憂或膽怯,他說:「就一個組織而言,我們絲毫沒有退縮。我們全公司的人幾乎無一例外,都認為這些抨擊只會讓我們更強調我們的重點。世界合作是我們的工作,因為一旦沒有合作,世界可能不存在,自然也沒有商務可言。我們相信在處理那套系列節目上,我們採取了正確的企業政策,但我不會說那是唯一正確的企業政策。我懷疑,要是我們都是伯奇協會的成員是否還會這麼做。」
威爾森繼續慢條斯理地說道:「讓公司在重大公共議題上採取立場這件事,會帶來許多問題,迫使我們不斷進行自我檢視。這是一種平衡的問題。你不能對什麼事都無動於衷,這麼做你只會拋棄自己的影響力。不過,你也不能在每一件重大議題上都採取立場。舉例來說,我們不認為在全國性選舉上採取立場是公司的責任──或許我們走運,因為索爾‧利諾維茲是民主黨,而我是共和黨。但像大學教育、民權、黑人就業這類議題,很顯然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希望,如果我們認為應該怎麼做,即使某個觀點不受眾人歡迎,我們也有勇氣堅持這個觀點。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碰上這種情況,那就是我們心目中的社會責任與良好的商業政策發生衝突。不過,這樣的時間點有可能來到,我們很可能有必要親上火線。舉例來說,我們默默地採取了一些行動,教育一些黑人青年,讓他們可以擔任清掃地板這類活動以外的工作。這項計劃需要我們工會的全面支持,我們也獲得了這些支持。不過,我透過一些微妙的方式知道,這項計劃的蜜月期已經過去,有人在暗中進行抵制。有些事情正在醞釀,如果讓它鬧大,可能會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業務難題。如果反對者不是幾十個人,而是幾百個人,事情還可能演成一場罷工。一旦發生這種狀況,我希望我們與工會的領導人,還能夠堅持立場盡力一搏。不過,我真的不知道。碰上這種事情,你真的沒辦法預測你會怎麼做。我只是認為,我知道我們可能該怎麼做罷了!」
之後,威爾森站起身走到一扇窗邊說,根據他的看法,公司現在必須做的一項重大工作,是維護公司賴以成名的個人與人性特質,而且這項工作在未來可能更加重要。他表示:「我們已經看到公司正在逐漸喪失這種特質的跡象。我們正設法向新進員工灌輸這種觀念,不過公司現在在西半球各地擁有兩萬名員工,和過去只在羅徹斯特雇用一千人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
我來到窗邊,與威爾森站在一起,準備告辭。就像早先有人對我說的,羅徹斯特在每年這個時候的天氣一樣,這是個濕冷、陰暗的早晨。我問威爾森,在這樣一個陰霾的日子,他可曾有過舊有特質能否維護的疑慮?他點了點頭說:「這是一場持久戰,我們能不能取勝還不一定。」
《紐約時報》暢銷書
Amazon.com商業類暢銷書Top1
全球兩大商業巨頭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共同推薦
「這本書是我讀過最棒的商業書。」──比爾‧蓋茲
福特汽車公司因推出愛德索新車慘虧3.5億美元,全錄以驚人的速度驟然崛起,奇異與德州海灣硫磺公司鬧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醜聞,但這些故事有什麼共同之處?它們每一個都是經典商業例證,說明一家標竿性公司可能因為特定一刻的榮光或惡名,帶給世人難以抹滅的印象。誠如這本睿智、有趣且發人深省的書所示,這些例子為我們帶來的商業教訓歷久彌新,直到今天仍然切身中肯。
有關華爾街的故事,總是充滿戲劇轉折與冒險,突顯財經世界奇謀詭計與變化多端的特性。本書作者布魯克斯見解獨到的報導,不僅非常深刻、具有人性,對重要細節歷歷如繪的描述,也讓人覺得無論是1962年美國股市駭人聽聞的重挫、一家著名經紀公司的瓦解,或是美國銀行家為拯救英鎊而採取的大膽行動,歷史都是不斷地重演。
在同樣迷人的主題上還有另外5個故事,成就了這本讀來令人興味無窮又獲益匪淺的故事集。長期為《紐約客》雜誌撰稿的布魯克斯,活潑、生動地說了12個永垂不朽的經典故事,從華爾街到各大城主街,美國企業與財經世界透過他的生花妙筆,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商業冒險》著實是最活潑、最有文采的真正財經新聞報導。
布魯克斯被《紐約時報》譽為「他那個時代的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本書獲得全球兩大商業巨頭比爾‧蓋茲(Bill Gates)與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致推薦,並譽為商業書經典代表之作。蓋茲表示:「在巴菲特把它借給我看20多年之後,在這本書首次問世45年以後,《商業冒險》仍是我讀過最棒的一本商業書。」
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 1920-1993
獲獎作家,因以財經記者身分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撰稿而享譽。除了《商業冒險》,還著有十本非文學類財經商業書,其中幾本對華爾街與企業世界有極具批判性的檢驗。在他的著作中,人稱經典的有《葛康達往事》(Once in Golconda)、《繁華盛世》(The Go-Go Years)與《商業冒險》。儘管布魯克斯主要因為財經相關議題的著作而揚名,他也曾經發表三本小說,並曾為《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與《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撰寫書評。
譚天(第1-7章)
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曾任聯合報編譯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等職。現旅居加拿大,專事譯作。譯有《戈巴契夫傳》、《新媒體消費革命》、《身先士卒》、《飛堡戰記》、《新工業國》、《探訪CEO》、《推動轉型的手》、《大事法則》與《當代最具影響力14位大師談創新》等約一百本書。
許瑞宋 suisung@kimo.com(第8-12章)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與責任編輯,亦曾從事審計與證券研究工作。2011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
譯有《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數位新分享時代》、《品格致勝》、《柏南克的四堂課》及《哈佛商學院最實用的創業課》等書。
重磅推薦
「本書作者布魯克斯真是說故事的行家……他的作品非常明確地提醒我們,經營一樁強盛事業與創造價值的規則仍然不變。舉例來說,每項商業行動背後都有人的存在,是不是有完美的產品、生產計劃與行銷手段都無關緊要,你還是需要合適的人來理解並執行這些計劃。……直到今天,布魯克斯對商業的深入見解,切題性仍然不減當年。」
──比爾‧蓋茲,《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文氣逼人,閱讀布魯克斯的書是一場盛宴。他的寫作能將原本令人眼神呆滯的主題,例如電氣產業市場定價醜聞等,化為喧囂歡樂的故事。而且,他還非常有趣。……他的故事精彩動人,以商業世界的特定時刻為背景,描繪出各式各樣栩栩如生的人物。」──《史雷特》(Slate)雜誌
「布魯克斯是他那個時代的麥可‧路易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看這本書是一項超級享受……布魯克斯是麥可‧路易士在創作上的直系先祖。」──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Business Adventures : Twelve Classic Tales from the World of Wall Street
譯者:譚天、許瑞宋
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2-11
ISBN:9789862135761
定價:480元 特價:88折 42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