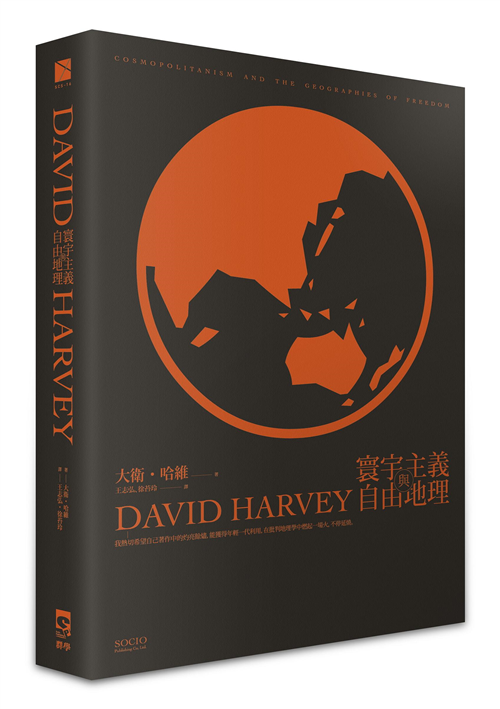
推薦序
序
前言
第一篇 普世價值
1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
2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
3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4 新寰宇人
5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
第二篇 地理知識
6 地理理性
7 時空與世界
8 地方、區域、領域
9 環境的性質
結語 地理理論與地理理性的謀略
註釋
參考書目
索引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以描述南印度班加洛(Bangalore)市區高爾夫球場上的頓悟經驗,來展開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他的球友指著「遠方兩棟閃亮的玻璃和鋼構建築,就在第一座果嶺後面」,建議他瞄準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或微軟(Microsoft)。在他抵達第十八座果嶺後(在前面九座果嶺曾遇見惠普〔Hewlett Packard〕和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佛里曼打電話給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他說,自由市場全球化和快速技術變革,造就了這樣的世界:
幾乎所有事物都數位化、虛擬化與自動化了。對那些能吸收新技術工具的國家、公司及個人而言,生產力的提升將很驚人。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階段,比起世界史的任何時刻,有更多人將能取用這些工具......。我認為,這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將證明具有極高的程度差異,以致這種差異最後將被視同種類上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引介世界已經從圓形變成扁平的想法。你所到的每一處,階層體制都遭逢來自底層的挑戰,或是自行轉變,從由上而下的結構變成較為水平的合作式結構......。此後,越來越多經濟體〔將〕是由人民的利益、需求和願望由下而上來治理,而非秉持狹隘統治集團的利益由上而下來治理。
佛里曼在不同國家旅行,與執行長、科技怪傑和權威人士會面,他發現他們在每個地方都將自己納入全球網絡、積極培育新技術的部署、創造前所未聞的效率,賺進大把鈔票更是不言可喻。他描述空前的技術和組織變革,尤其在資訊科技(IT)部門(在某個地方,他甚至樂於認罪,接受技術決定論的指責,但誤將這種理論歸諸馬克思,大量引述《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在這背後,有著重大的宏觀經濟改革。最初由「像中國、俄羅斯、墨西哥、巴西和印度這些國家的少數領袖」率先實施(往往仰賴威權國家權力來達成目標),一個接著一個國家被推到「更偏向出口導向的自由市場策略—奠基於國營公司私有化、金融市場解除管制、幣值調整、外國直接投資、縮減補助金、降低保護主義關稅壁壘,以及引進更彈性的勞動法律」。他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面臨「不可否認的事實,即更開放而競爭的市場,是扶持國家擺脫貧困的唯一可持續載具,因為市場是使新觀念、技術及最佳作法輕易地流入你的國家,以及令私人企業、甚至政府具有競爭誘因和彈性來採納新觀念,將它們轉化為工作和產品的唯一保證」。不過,一個國家要成功,還要有其他兩項必要條件。首先,國家必須刺激創新,並建構有利於創業精神,以及個人承擔與負責的管制環境。建立這種良好商業環境,正是經濟成功的神奇配方的由上而下部分。其次,同時也必須有由下而上、基層文化理解方面的轉變。一國人民必須內化「勤奮工作、節儉、誠實、耐性與堅韌的價值」,並且「對改變、新科技和女性平權保持開放」。換句話說,如果他們和他們定居的國家,要在當今競爭環境中獲得成功,每個人都得擁抱當代資產階級美德及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和康德的寰宇主義一樣,為了符合進入普世(此例為新自由主義)權利和福祉體制的資格,我們在每個地方都必須變成一個模樣。
佛里曼的著作,是針對近來極為盛行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一幅出色但言過其實的諷刺畫。這本書顯然抹除了地理學與人類學差異,雖然偶爾這些差異看似確實造成了有待克服的障礙。私有財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普遍體系,一起構成了享有特權(若非唯一)的制度框架,令自主與自由的普世美德得以實現。這就是據稱的「不容辯駁事實」,依佛里曼之見,我們期盼的美好未來都得寄託於此。布希總統(不在佛里曼偏愛的政治家之列)提出了類似論點:壓迫、怨恨與貧窮,將處處遭遇「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反擊,因為這些已證實了「它們抬升整個社會以擺脫貧窮的能力」。
這類理論存在已久,但1947年,以馮.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其他幾位為首的一群卓越人士,組成朝聖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時,才顯露了這類理論獨樹一格的當代特色。他們宣稱個人權利,包括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在各處都因為「蒙受專斷權力擴張」,以及「越來越少人信奉私有財產和競爭市場」而「逐漸削弱」,加以「缺乏跟這些制度相關的分散權力及創制,就難以想像一種能有效保障自由的社會」。因此,挾著壟斷性暴力的國家,其角色在於創造和支持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實作,並促進貨幣健全和良好商業環境。不過,國家不應該做得更多,因為根據該理論,國家不可能擁有足夠資訊來預測市場信號(價格),而且因為有權有勢的利益團體(如惡名昭彰的「K街」說客〔K Street lobbyists〕,目前腐化了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將無可避免為了己利而使國家干預遭受扭曲,產生偏見。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在培植私有財產的迷思,視之為自主和自由的擔保人上,格外殷勤。他們將鑲嵌在(當時的嚴肅學者,如葛洛休斯〔Hugo Grotius〕和亞當斯密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的那種)道德責任的社會系統裡的18世紀私有財產美德觀點,轉變為一種絕對物神崇拜(fetish),將財產視為不受約束且排他性的個人權利,即隨個人高興來處置他擁有的東西。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對私有財產權行使的任何限制,都被解釋成違憲的「徵收」形式。在佛里曼讚賞的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絕妙創新著作」中,闡明了這種物神信念。5德索托通常被描述為來自秘魯的本土「第三世界理論家」,但事實上,他在日內瓦長大並接受教育,而且早期曾獲右翼北美新自由主義智庫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Atla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資助。靠著基金會的資金與建議,德索托在秘魯利馬(Lima)成立他的自由與民主研究院(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旋即成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主導傳聲筒之一。柴契爾、傅利曼和一大群其他新自由主義傑出人士,認可他是本土思想家,他出版的書成了國際暢銷書,在發展理論(包括世界銀行的理論)上極具影響力。
德索托認為,全球南方的貧窮是自找的,而不是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或資本主義造成的:主要的發展障礙是資產的擁有(尤其是土地和房屋)欠缺明確的權利。所有權會向信貸市場敞開大門,並將非正式經濟裡的人整合進入全球市場,從而終結貧窮。德索托想法的落實,剛開始是在他的指導下,但後來由秘魯政府接手,隨後由世界銀行接管,並未替在秘魯獲得所有權的120萬人產出預期結果。一個實質效果似乎是大人工作時間更長,他們的小孩工作時間減少。這一點備受世界銀行和主流報刊,以及佛里曼稱讚為正面結果。不過,誠如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的說明,這個結果比較可能是反映了資料蒐集方式,而非人們的日常生活;我還要補充一點,即使這項結果屬實,但認為這有利於工作時間更長的人,而非裨益於他們為其工作的人,這種想法一點根據也沒有。
無論如何,認定作為普世價值的個人化私有財產,為經濟發展和減緩貧窮的必要條件,是沒有歷史根據的。英國位居起點,主導了逾一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世界,同時,皇家、教會、牛津與劍橋學院,以及少數貴族家庭,掌控了約三分之二的土地。實際上,將財產權授予貧困人口,會使得他們蒙受市場剝削。在埃及,將過去所謂的「非正式經濟」再概念化為私有財產導向的「微型企業」經濟(遵循德索托推薦的路線),並納入「微型貸款」的信貸架構,結果誠如艾利埃恰(J. Elyachar)的報導,一點也稱不上仁慈。它試圖將市場評價和規訓強加於傳統工作坊文化,並以相當高的報酬率從該文化萃取出價值。新自由主義者盛讚這類計畫,但真實的結果如艾利埃恰所述,卻是創造了一個「奪取的市場」(market of dispossession)。隨著小額信貸越來越受吹捧為全球貧窮的解答,現在這種作法在全世界日漸壯大。起初是一種非商業方案,向大量赤貧民眾(尤其女性)提供極少量資本,現在商業金融機構吹噓小額信貸計畫是將大量人民納入市場規訓裝置,同時抽取高額報酬率(某些案例高達20%)的辦法。將慈善小額信貸轉變為具商業可行性的微型金融系統,有其重大意義。這是嘗試實施佛里曼所主張的,對創造新自由主義之平坦世界至關重要的文化變革(一種自我規訓裝置)。現在,這已折射到慈善實踐裡。葛洛斯(David Gross)指出,一群(以華爾街風格培養出來的)新興慈善家如今相信,「要有效對抗貧窮端賴創辦低薪工廠,並建立索取許多美國人視為高利貸之利率的貸款機構。」
認為窮人越是蒙受市場規訓——以及,附帶地遭受富人剝削——就越能獲益,這種驚人觀點一點也不稀奇。稍早於1970年代中期,透納(John Turner)受無政府主義者啟發的著名倡議,於全世界棚戶區與貧民窟裡興建自助式住宅(self-help housing),麥可納馬拉(McNamara)的世界銀行則欣然地予以利用,當成減輕貧窮和低度發展痛苦的關鍵。眾人預想這能導向一種適用於所有人的民粹主義資本主義,從而消除貧窮。這個方案沒能實現目標(雖然有些中間人變富裕了),貧窮更甚以往,一如最近有關我們「貧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狀態的報導裡,令人難堪的記錄。我們應該要記得,葛洛休斯和亞當斯密很久以前的堅決主張,即唯有調節社會互動的「道德情感」達到必要的品質,私有財產權的安排才有機會運作。因創辦非商業性小額信貸方案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尤納斯(Yunus),納入了這種道德元素,但如今無數以商業為基礎的微型貸款方案,卻沒這麼做。
新自由主義者沒去想像強行實施私有財產權,以及基於各種地理、生態及人類學情境來貨幣化市場機構的後果,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更驚人的自負之一。例如2003年,美國要求佔領下的伊拉克,實施全體國有資產和企業的私有化、外國公司得以握有伊拉克公司的完整所有權、開放伊拉克銀行接受外國控制、外國直接投資伊拉克或將利潤匯回本國零障礙,以及消除幾乎所有貿易壁壘。企圖在伊拉克實施這種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毫不考慮該國的複雜社會結構與歷史,導致伊拉克政治經濟的災難性崩潰。然而,偏袒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轉向,自1970年代以降,在雷根主政的美國及柴契爾主政的英國發動市場改革的大張旗鼓引領下,已在全世界蓄勢待發。從1945年至1970年代中期止,主導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發展型、干預主義的統制國家(dirigiste state),一點一滴地沿著傾向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改革。在某些例子(如1973年政變後的智利)裡,則是以激烈方式展開變革。在其他案例中,新自由主義改革則是被迫作為嚴重財務危機之部分解決方案而實施。例如,許多先前成功的東亞和東南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歷經1997-98年災難性的債務危機,被迫進入局部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其他地方改革的推動,則是結合了外部壓力(通常是由美國財政部來指揮協調,通過它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控制來運作)和內部動力(地方菁英試圖從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獲得政治經濟利益)。
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詳細分析,新自由主義據稱是1970年代經濟危機的解藥而崛起的過程。雖然原則上,新自由主義化許諾一個免於過度國家干預的自由世界,但實際上,國家卻積極介入塑造良好商業環境(往往是補助資本,卻抑制勞工的願望)、在金融機構遭受威脅時出手相救,以及通過公私合夥(和其他治理結構)或選舉過程的合法腐敗(於是有那些華盛頓的說客),將企業整合進入政府。新自由主義化也許諾了快速經濟成長和世界市場擴張,而其回報將有益於全體。實際發生的卻全然是另一回事。整體而言,新自由主義未能刺激全球性的成長。但它確實要求不斷抨擊各種社會團結形式,因為它們不見容於奠基在個人責任與個人進取上的系統。我們也見到國家大幅度地撤離了社會供應。減少貿易壁壘和開放全球市場,有助於經濟活動區位的快速移轉,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去工業化的巨浪,以及勞工階級社區、甚至整個城市區域裡的社會斷裂。「境外轉包」(offshoring)成了眾所皆知的用語。雖然與日俱增的貿易賺得了收益,但這些收益在地理和社會上分配不均。比如說,金融資本的勢力大幅提升,而組織化勞工的力量則大幅削弱,因為國家紛紛相繼針對勞動市場實施更高的彈性,有時候舉措十分激烈。此外,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倡議者,在教育界(大學,以及富裕捐助者和企業於1970年代期間成立的許多智庫)、媒體、企業董事會與金融機構、重要政府機構(財政部、中央銀行),以及那些管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中,佔據了極具影響力的位置。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在作為普遍性論述模式,以及全球公共政策基礎方面,都取得了霸權。它逐漸界定了許多人藉以詮釋、棲居及理解這個世界的常識之道。我們現在全成了新自由主義者,還往往無所覺察。
重返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的知識教育
探索實現真正寰宇主義的困境與可能性
自主(liberty)與自由(freedom)經常被召喚來正當化政治行動。世界霸權總是將政策奠基於這些尊貴概念的某種版本。但實際上,理想主義的議程經常在面臨特殊具體環境時就變了調。各地美軍監獄的虐囚事件、伊拉克佔領造成的劇烈傷害,一再顯示出對於自主和自由的追尋,會導致暴力與壓迫,破壞世人對於寰宇主義的信賴。
哈維試圖描繪出一種新的寰宇主義秩序,該秩序更適合解放且自主的全球治理形式。他主張,過往政治議程失敗的根源是忽略地理與文化的複雜性。因此,將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知識納入社會與政治政策形構,是真民主的必要條件。
哈維首先針對自由和自主的政治運用,尤其是布希政權時期的作法,提出饒富洞見的批判。接著,透過對於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如空間、地方及環境)的存有論探究,徹底將地理學重新架構為社會理論和政治行動的基礎。此外,他剖析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世界是平的》等暢銷書所隱含的知識預設及盲點。
一如哈維的所有著作,《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組織清晰,寫作風格自信而熱切。書中跨領域的廣泛論證既富原創又深具挑戰,各種主張值得重視。本書的論點和意蘊肯定會激起諸多討論。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當代最富盛名且最廣受徵引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與社會理論家。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牛津大學,目前擔任紐約市立大學(CUNY)「地方、文化與政治中心」(Center for Place, Culture, and Politics)主任。著書二十餘冊,涵蓋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變遷研究,以及都市化、不均地理發展、帝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議題。中譯作品包括《巴黎,現代性之都》、《新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資本的空間》等。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群學出版社「空間與都市研究譯叢」擘畫者,編著《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
徐苔玲
東華大學教育所碩士、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長期參與「空間與都市研究譯叢」譯事。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約翰.藍儂唱道"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麥可.傑克遜唱道"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歷史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曲唱著「千古江山如詩如畫,
還我一個太平天下」
《共產黨宣言》寫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湯瑪士.佛里曼在印度班加洛市的高爾夫球場,打電話給他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
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持續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進行他獨特而深刻的解殖計畫,在這本火花四射般地動員了高度人文社會知識碰撞、極具思想啟發性與時代意義的鉅著中,他的手術刀,切入一個更核心、更根本的底蘊:自由寰宇主義的普世價值論——一套內育於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康德的寰宇主義、盧梭的意志理性論、洛克的私有財產及權利的法律政治學組裝。哈維詰問,當國際霸權經常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修辭,來正當化各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破壞行徑時,我們如何應對「普遍權利」與各種替代性的普世化計畫?除了自由寰宇主義的版本外,其他寰宇主義之希望空間的開拓又如何可能呢?
伴隨著對全球化的反思,寰宇主義(cosmopolitanism)——一如周禮中的世界大同這般淵遠流長的社會思想——的各種倡議與政治社會實踐,在國際上引發了強烈的迴響與論辯,這個複雜議題的復甦,我認為對台灣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哈維這部堪稱博大精深的作品,來得正是時候,無疑是對當代寰宇主義最佳的知識基礎。
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里曼的書名《世界是平的》,新自由主義一向擅於動員啟蒙神話,打造著烏托邦的平坦世界,哈維直接面對其背後的自由寰宇主義基礎,進行刨根式地深刻解構。他引用了後殖民與後結構主義元素加以批判,但未滑入若干「後學」的懷疑主義陷阱,他更認真地與多位看似同道、實則有別的重要批判思想家,如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貝克(Ulrich Beck)、黑爾德(David Held)、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傅柯(Michel Focault)等人,系統地展開真刀真槍的交鋒,理論對話堪稱經典,令人大呼過癮。哈維最後透過根基同樣深厚的歷史地理唯物論,堅持「從支持或反對啟蒙的知識勒索中解放出來」,批判地重構了社會—生態、時間—空間以及地方領域的辯證理論,並據之鋪陳他「地理理性的謀略」,以為重建真正自由的、解放的寰宇主義社會制度鋪路。
這是一部我相當激賞的作品,喜歡文學的哈維,他充滿地理學想像的文字,除了社會科學的精準嚴謹外,總是帶著一股藝術氣質。打開這本書,彷彿就展開了一段奧德賽史詩般的時空征程,在寰宇世界的崎嶇地表上,匍匐前進,之後你又不自主地會想爬回到自身所處的情境性(situatedness),這進出之間,不管多麼嚴苛,靈感、領悟與力量不斷湧現。
舉幾個跟台灣切身相關的情境,比如說跨界流動中公民權與國境的爭議,我們要如何面對移民與移工?是以康德式良善的臨時「款待權」原則?只有那些「表現成熟」的人,才會被國家賦予永久的居留權?國族主義本身,可說就是一種版本的寰宇主義,如康德的「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建議,唯一行得通的寰宇政府形式,是以獨立的國族國家組成的邦聯為基礎。這或許是個好主意,或許是爛主意,不過哈維至少同意康德的一個基本前提,任何寰宇主義的普世性計畫,不管是基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宗教、環境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需要作為界定「可能性條件」的地理學與人類學基礎,而不只是神學、宇宙論這種純粹形而上的思辨或觀念論。哈維獨到之處,在於剖析這個寰宇主義構想背後,康德自認為具有「科學基礎」、實則大有問題的人類學與地理學觀念——國族國家是以共同血統為基礎的市民社會,至於那些「不合格公民」乃至於「麻煩元素」,主權國家總是有權將之摒除在公民權利之外。
國族主義與寰宇主義大有相互滲透的可能,然而國族國家的僵固與連貫性也不斷遭受挑戰。以「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寰宇主義框架,作為處理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與法律問題的各種倡議,正不斷將知性、秩序和課責,建構到諸如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這類具體的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場域。又如我們念茲在茲的「聯合國」——某種形式的寰宇政府,十餘年來高調提倡企業社會責任(CSR)與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視其為調控資本主義的全球治理,被跨國企業菁英奉為圭臬——是另一個標榜普世價值的寰宇主義版本。在聯合國人權公約與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下,「國際勞動標準」(global labor standard)被視為普世的人權價值,一系列用來衡量勞動標準被遵循與否的企業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指標,及其監督、稽核的操作執行,被系統性建立(如工時、童工、環境安全、性別歧視等),弔詭的是,核心的勞動標準「勞動三權」(勞工團結權、集體協商權、罷工權),在這樣的市場化體系中,只是幾百項量化指標之一,因而富士康的勞動條件改善率,被蘋果委託的「公平勞動協會」(FLA)評定為達到99%。
像CSR這種全球治理的寰宇主義版本,其背後的普遍權利觀點,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私有產權的權利論述,這是合宜的權利觀點?哈維不留情面地批判了貝克的寰宇人權以及黑爾德的寰宇民主體制,認為它們過於貼近新自由主義而令人不安,對洛克式資產階級民主不抱希望,哈維在書中轉而尋求另類的出路——將社會運動的多樣思想與實踐,納入普遍權利的求索。例如楊恩(Iris Marion Young)對照著她所謂的普遍壓迫的五種面貌,來定義普遍權利,這五種面貌包括:勞動剝削;因身分認同而遭到邊緣化;缺乏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生活的資源;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內在於家庭和社會的暴力。很明顯地,經由各種集體行動與社會團結,來解除這些壓迫的權利,已超出新自由主義組裝的規範,然而這些才是合乎正義的普遍權利。
普遍權利主張湧現的另一個脈絡,是面對資本主義的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ession),各地人民所採取的社會自體防禦(social self-protection)。哈維細細解讀,不同於過去資本主義對於勞動剩餘價值的主要剝削方式,當代的奪取式積累,是零散而分殊的過程——山也BOT、海也BOT、這片要徵收、那區要都更,還有各式各樣的民營化、自由化、私有化、血汗勞動、關廠外移、環境剝削、原住民文化危機、生態破壞、金融泡沫等等;為了抵抗這一切壓迫的地理具體性和特殊性,社運團體與NGO運用了人權、尊嚴、生態權與環境權等普遍權利修辭,以作為統一的對抗政治基礎。例如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在台灣的司法改革中,被導入並策略性地運用,憲法對於財產權的保障,被引為土地正義運動之法律正當性來源。然而面對寰宇主義的缺陷,當然有理由質疑普遍權利的拜物教傾向,以及其背後混沌不清的人類學、地理學與生態學知識假設;像是「我是人,我反核」這句口號,在社會運動與知識圈內,就曾引發不小的爭論,這種曖昧的類存在(species being),是什麼樣的人呢?本真人?自然人?無差別的人?然而哈維提醒著我們,必須十分警覺於新自由主義化與普遍性、倫理原則及人權等訴求之間,所塑造出來的關鍵連結,如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配,需要實施某一套普遍權利,那麼對這套支配系統的抵抗,也需要爭取不同的權利鬥爭與社會團結,建構另一套普遍權利概念,並務實地將其原則納入法律。
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地理學者,他對當代各種擁保地方原真性(authenticity)——環繞著海德格的現象學哲學,要求「地方充盈」(placefulness)必須優先於自由寰宇主義的「平坦地球」,訴諸於「在地性」(localness)作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逃逸路線,如數家珍;然而對於像艾斯科巴過於浪漫化的地方主義取向,哈維也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他選擇了一條不容易但在我看來頗為實在的路徑,關懷著如何將「戰鬥性地方主義」(militant particularism)辯證而有機地連結上「全球團結胸懷」(global ambition),開創「地理理性的謀略」,而避免流入內閉保守的地方法西斯排外主義。
我想,哈維是認真地看待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他來說,這絕非神話,於是,他接過並轉化了寰宇主義者努斯鮑姆的問題意識:需要怎樣的人類學與地理學知識,作為進步性寰宇主義之可能性情境? 對於人文地理學有興趣的讀者,會驚艷於,哈維以獨到的歷史地理唯物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環節方法」,批判地重構環境、時空性、地方/區域等概念,開展精采的新寰宇主義解放地理,為真實世界的空間實踐鋪路。如同他一貫主張的實踐主義地理學方法,他在文末所表達的對於當紅左翼理論家如哈洛威(John Holloway)、巴迪烏(Alain Badiou)、紀傑克(Slavoj Zizek)等人的不滿意,即在於他們的貧弱地理向度關懷,忽略了空間做為關鍵字的重要性,以至於限制了政治實踐的理論動能。
我必須承認自己是個哈維粉絲,我個人跟哈維有幾次近距離的接觸,除了一般的國際學術會議之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跟他在印度孟買開會,並於會後到農村去做關於徵地抗爭的田野訪查;另一次是他來台灣訪問,去參訪抗爭中的樂生療養院,我們曾以研討會論文的形式,就樂生保留運動的國際串聯(聯合國相關人權機構、NGO、跨國法律訴訟等等)如何與社區組織及運動論述結合的經驗,跟哈維交流。他的論述極富創造力,犀利而務實,政治關懷與敏銳度,始終如一。多年來我受哈維思想的啟迪,高度推崇他的成就,也為他平易近人的人格特質所吸引,他的著作始終是我愛用的教材,在王志弘等人以及群學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哈維近來的著作,得以透過靠譜且閱讀性極高的中文版本,持續與台灣讀者見面。個人除了高度推薦這部作品之外,也深切期待哈維其他作品的出版,共饗讀者。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譯者:王志弘、徐苔玲
出版社: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2-05
ISBN:9789866525797
定價:500元 特價:9折 450元 |